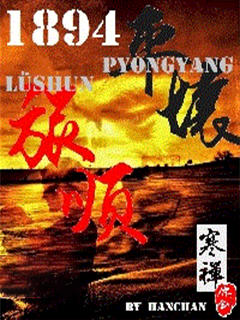- [ 免費 ] 前言
- [ 免費 ] 第壹章
- [ 免費 ] 第二章
- [ 免費 ] 第三章
- [ 免費 ] 第四章
- [ 免費 ] 第五章
- [ 免費 ] 第六章
- [ 免費 ] 第七章
- [ 免費 ] 第八章
- [ 免費 ] 第九章
- [ 免費 ] 第十章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三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四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五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六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七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八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九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三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四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五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六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七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八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九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三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四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五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六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七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八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九章
- [ 免費 ] 第五十章
- [ 免費 ] 第五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五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五十三章
- [ 免費 ] 第五十四章
- [ 免費 ] 第五十五章
- [ 免費 ] 第五十六章
- [ 免費 ] 第五十七章
- [ 免費 ] 第五十八章
- [ 免費 ] 第五十九章
- [ 免費 ] 第六十章
- [ 免費 ] 第六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六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六十三章
- [ 免費 ] 第六十四章
- [ 免費 ] 第六十五章
- [ 免費 ] 第六十六章
- [ 免費 ] 第六十七章
- [ 免費 ] 第六十八章
- [ 免費 ] 第六十九章
- [ 免費 ] 第七十章
- [ 免費 ] 第七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七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七十三章
- [ 免費 ] 第七十四章
- [ 免費 ] 第七十五章
- [ 免費 ] 第七十六章
- [ 免費 ] 第七十七章
- [ 免費 ] 第七十八章
- [ 免費 ] 第七十九章
- [ 免費 ] 第八十章
- [ 免費 ] 第八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八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八十三章
- [ 免費 ] 第八十四章
- [ 免費 ] 第八十五章
- [ 免費 ] 第八十六章
- [ 免費 ] 第八十七章
- [ 免費 ] 第八十八章
- [ 免費 ] 第八十九章
- [ 免費 ] 第九十章
- [ 免費 ] 第九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九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九十三章
- [ 免費 ] 第九十四章
- [ 免費 ] 第九十五章
- [ 免費 ] 第九十六章
- [ 免費 ] 第九十七章
- [ 免費 ] 第九十八章
- [ 免費 ] 第九十九章
- [ 免費 ] 第壹百章
- [ 免費 ] 第壹百零壹章
- [ 免費 ] 第壹百零二章
- [ 免費 ] 第壹百零三章
- [ 免費 ] 第壹百零四章
- [ 免費 ] 第壹百零五章
- [ 免費 ] 第壹百零六章
- [ 免費 ] 第壹百零七章
- [ 免費 ] 第壹百零八章
- [ 免費 ] 第壹百零九章
- [ 免費 ] 第壹百壹十章
- [ 免費 ] 第壹百壹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壹百壹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壹百壹十三章
- [ 免費 ] 第壹百壹十四章
- [ 免費 ] 第壹百壹十五章
- [ 免費 ] 第壹百壹十六章
杏書首頁 我的書架 A-AA+ 去發書評 收藏 書簽 手機
简
第四十七章
2018-5-28 06:01
第四十七章 形勢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“其軍紀訓練以英國為師……紀律極其嚴肅,武器保養、艦內配置非常完善……口令均用英語,艦內部署表、日程表等文件則用中英雙文……水兵們動作迅速,敏捷,姿勢準確。其跨國遠行不多,於本國航行則非常頻繁,然從未發生任何事故。1889年旅行演習時,艦隊出港迅速、隊形保持良好……這絕對不是可以輕侮之對手。”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“雖然屢有倭人北上之信,但目下他們的主力應該還在漢城,另外龍山、臨津、朔寧三處則各有倭兵約兩千。”薛雲開對於剛才受辱始終是深深不忿。
說到軍務,馬凱清也不計前嫌說:“他們應該是等元山之兵。”其說的是日軍七月初在朝鮮東岸的元山港登陸的部隊,左寶貴在赴平壤途中也得知此消息。
“目下漢城到底有多少倭兵?”左寶貴也開始忘了剛才和馬凱清的齟齬,壹副精神都放在當前中日對峙的形勢上。
“漢城的電報已斷,而龍山、臨津、朔寧為南下漢城要道,咱們的探弁過不去,所以不知道漢城的虛實。還有,平壤漢城間也有他們的遊兵散勇……”說到這兒馬凱清臉色壹沈:“咱們派出去十多隊的探弁,能回來的連壹半也沒有,可能已經遭遇不測,所以知道這些已經不易了!”
薛雲開也眉頭輕皺,邊吃菜邊說:“中堂很早說過,倭人兵力應該在幾千到壹萬之間,但那是在倭人增兵釜山以前。增兵以後,我只聽盛觀察提過,謂葉軍門說在成歡與倭人開仗時有萬六千人,還未算釜山的兵……此數雖有誇大之嫌,但元山起碼也有數千人,所以……咱們估計,倭人在朝鮮應最少有兩萬之眾。”
左寶貴自言自語道:“幸虧元山之兵正南下漢城……”
馬凱清喝壹口酒說:“元山往平壤的路很難走,翻山涉水,走到這兒肯定人困馬乏。”
“那,他們會不會冒險直接從大同江口登岸呢?之前聽說那裏有倭船出沒。”
馬凱清給薛雲開斟酒說:“那應該是虛張聲勢。那裏沒有象樣的港口,登岸壹定要大量駁船,那裏船不多,勉強為之只讓咱們和北洋水師有機可乘,何況沿著朝鮮西岸的江口都有咱們的探弁。”
“妳說他們的主力還在漢城,這是幾天前的消息?”
“消息是探弁回黃州拍的電報,電報是三天前拍的,從前方到黃州用了兩三天,所以現在說的已經是約四五天前的情況了。”
“元山有咱們的探弁嗎?”
“早就派去了,不然怎麽知道倭人南下呢?”薛雲開應道。
左寶貴眼睛轉了轉,仍然沒有釋懷,喝了口茶,手捋胡子說:“咱們現在在黃州有多少人?”
薛雲開邊嚼邊道:“半個哨……”
“半個哨?!”左寶貴瞪大眼睛道:“黃州為平壤與漢城間的重鎮,怎麽只有半個哨?”
“這麽大的平壤,目下還不足萬人,後路也要處處留人,還有多少人可以調動呢?咱們還要加緊鞏固平壤的防務哪!”薛雲開開始不耐煩,僵硬的笑容也早就消失,聲音也更為低沈,畢竟他今天只道和兩人喝喝酒,“輕松輕松”而已,沒想到左寶貴就是不想讓自己輕松。
“趁倭人還未增兵,我想,咱們應該趕緊南下。”
左寶貴輕輕的壹句,房間裏馬上變得寂靜,薛雲開夾菜的手也停在半空,連咀嚼的聲音也沒了。馬凱清也怔了怔,臉側向左寶貴,正提起酒杯的手也緩緩放下。
沈靜半晌,薛雲開終於忍不住,咽了壹口,嗤笑道:“如此兵單,怎能還分兵漢城?”
然而左寶貴還是壹臉嚴肅:“兵是不多,去不去漢城也可以再斟酌,但關鍵是,和倭人壹樣,先據守四周之險,使對方不能裕如赴平,咱後路的援兵就能相機前進。”
左寶貴說的其實也不是沒有想過,薛雲開慢慢地斂起那“笑容”,坐直了腰,臉色又冷起來,籲了口氣,凝思片刻,眼睛斜著桌子上的杯子說:“平壤與漢城相距千余裏,要是南下,必定難以通氣,且容易被倭人從中攔截,或繞過咱們出擊之師直取平壤。若處處留兵,咱前方和平壤之兵就更少了。”
左寶貴反駁道:“現在不是他們北上就是咱們南下,誰沒有通氣之虞?誰不怕被對方從中攔截或?何況中朝壹衣帶水,咱們後方援兵陸續繼至,反觀他們隔海而來,背水而戰,比咱們還艱難,隨帶糧食也必定不多,為何人家還敢銳意北上,而我等卻龜縮不前呢?”
“說起糧食……”本來壹時間也難以反駁,但最後聽見“糧食”,就馬上想到了。薛雲開擱下筷子,雙手放在桌上,看著眼前壹桌的飯菜,冷冷地笑了笑,但又像是苦笑:“這可又是壹大難處呀!咱們為求先進平壤,都是人先走,而糧草在後。但現在也快壹個月了,盛軍國內的糧草才剛到旅順,就算到了義州,也得像毅軍的糧草壹樣,不知何時才能過江,過了江的還要沿那條該死的朝鮮後路上轉運,目下咱們隨帶的軍糧還有在路上的呢!我想,貴軍也好不到哪去吧?”
見左寶貴默默地聽著,沒有回話,薛雲開繼續道:“目下平壤已近萬人,吃的都是隨身攜帶的那丁點的糧食,咱們雖已委托平安道就地籌措,但物價就隨之上漲。雖說朝鮮物價便宜,但平壤的百姓也得吃的呀!還未說即將到來的蘆榆防軍和各路援師?妳說,如此境況,如何南下?”
然而左寶貴卻好像早就想過這問題,盯著薛雲開道:“既然平壤是養不起這麽多人,那咱們就更應該分兵駐紮,此其壹。其二,現在開始秋收季節,而平壤漢城之間農田眾多,我想應該沒有糧食之虞。其三,我也說了,咱們南下不壹定要去漢城,只據守四周之險,最多出行數百裏,要是糧食遠在義州,那在黃州還是在平壤又有何區別?”
薛雲開反駁不了,細起眼睛看著左寶貴,眼冒寒光。老實說,薛雲開雖然縱情酒色,但習慣武人相輕的他絕不是泛泛之輩,而他亦有心再官升壹級,所以他此番被派來此地,絕不像那些盲目自大的官兵,相反,他早就聽說過日軍近年勤練西法,務求脫胎換骨,也早就想過眾多對策,這也是為何他老覺得兵力太單。
但他始終認為,以壹萬兵力死守平壤,靠著平壤的天險和雄偉的城墻,縱是惡戰,相信倭人亦難壹舉攻下。而時日壹長,也就如左寶貴所說,後方緩師陸續趕至,對倭人必然不利,那時候再南下漢城也不為遲。故在薛雲開看來,其他任何策略都得冒不必要的險。
但最重要的還是,作為北洋嫡系的他,早就收到壹意主和的李鴻章的指示,絕不能孟浪進兵。這和其海戰思維如出壹轍,重兵之駐平壤猶如水師之守渤海,兩者都只作“猛虎在山之勢”,務求以逸待勞。畢竟,盛軍、毅軍和北洋水師都是李鴻章的家當,打光了自己也完了。何況,所謂的四大軍已經是東拼西湊,壹時三刻也實在難以再擠出什麽援兵來。故即便薛雲開真覺得左寶貴的話有理,也絕不敢去改變李鴻章親自定下的策略。
至於左寶貴則已離開北洋多年,此次奉軍為四大軍之壹,也是由李鴻章出面請裕康而非直接調遣。故李鴻章其實是不太好意思對奉軍指手畫腳的,但同時也不會向其透露其心裏的盤算,當然這也可以免得左寶貴摻和。至於對李鴻章唯命是從的薛雲開,對於這個由上司請來的左寶貴,即便對他更不滿,也不好意思隨意拿上司的話來壓他。
故此刻的薛雲開也不想再反駁左寶貴,也沒心思去思量如何反駁,只道他欲爭功,又或是輕敵,緩緩道:“左軍門呀……妳有妳的道理,但妳說的,終究還是冒進。此次倭人來勢洶洶,有備而來,咱萬不可以輕敵,葉提督的捷報,未必可信。我看,咱們應該先固後路,後圖進取為妥。”
“我就是不輕敵才有此議,”左寶貴鼻子吭氣道:“至於葉提督的捷報,我壓根就不信!”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“其軍紀訓練以英國為師……紀律極其嚴肅,武器保養、艦內配置非常完善……口令均用英語,艦內部署表、日程表等文件則用中英雙文……水兵們動作迅速,敏捷,姿勢準確。其跨國遠行不多,於本國航行則非常頻繁,然從未發生任何事故。1889年旅行演習時,艦隊出港迅速、隊形保持良好……這絕對不是可以輕侮之對手。”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“雖然屢有倭人北上之信,但目下他們的主力應該還在漢城,另外龍山、臨津、朔寧三處則各有倭兵約兩千。”薛雲開對於剛才受辱始終是深深不忿。
說到軍務,馬凱清也不計前嫌說:“他們應該是等元山之兵。”其說的是日軍七月初在朝鮮東岸的元山港登陸的部隊,左寶貴在赴平壤途中也得知此消息。
“目下漢城到底有多少倭兵?”左寶貴也開始忘了剛才和馬凱清的齟齬,壹副精神都放在當前中日對峙的形勢上。
“漢城的電報已斷,而龍山、臨津、朔寧為南下漢城要道,咱們的探弁過不去,所以不知道漢城的虛實。還有,平壤漢城間也有他們的遊兵散勇……”說到這兒馬凱清臉色壹沈:“咱們派出去十多隊的探弁,能回來的連壹半也沒有,可能已經遭遇不測,所以知道這些已經不易了!”
薛雲開也眉頭輕皺,邊吃菜邊說:“中堂很早說過,倭人兵力應該在幾千到壹萬之間,但那是在倭人增兵釜山以前。增兵以後,我只聽盛觀察提過,謂葉軍門說在成歡與倭人開仗時有萬六千人,還未算釜山的兵……此數雖有誇大之嫌,但元山起碼也有數千人,所以……咱們估計,倭人在朝鮮應最少有兩萬之眾。”
左寶貴自言自語道:“幸虧元山之兵正南下漢城……”
馬凱清喝壹口酒說:“元山往平壤的路很難走,翻山涉水,走到這兒肯定人困馬乏。”
“那,他們會不會冒險直接從大同江口登岸呢?之前聽說那裏有倭船出沒。”
馬凱清給薛雲開斟酒說:“那應該是虛張聲勢。那裏沒有象樣的港口,登岸壹定要大量駁船,那裏船不多,勉強為之只讓咱們和北洋水師有機可乘,何況沿著朝鮮西岸的江口都有咱們的探弁。”
“妳說他們的主力還在漢城,這是幾天前的消息?”
“消息是探弁回黃州拍的電報,電報是三天前拍的,從前方到黃州用了兩三天,所以現在說的已經是約四五天前的情況了。”
“元山有咱們的探弁嗎?”
“早就派去了,不然怎麽知道倭人南下呢?”薛雲開應道。
左寶貴眼睛轉了轉,仍然沒有釋懷,喝了口茶,手捋胡子說:“咱們現在在黃州有多少人?”
薛雲開邊嚼邊道:“半個哨……”
“半個哨?!”左寶貴瞪大眼睛道:“黃州為平壤與漢城間的重鎮,怎麽只有半個哨?”
“這麽大的平壤,目下還不足萬人,後路也要處處留人,還有多少人可以調動呢?咱們還要加緊鞏固平壤的防務哪!”薛雲開開始不耐煩,僵硬的笑容也早就消失,聲音也更為低沈,畢竟他今天只道和兩人喝喝酒,“輕松輕松”而已,沒想到左寶貴就是不想讓自己輕松。
“趁倭人還未增兵,我想,咱們應該趕緊南下。”
左寶貴輕輕的壹句,房間裏馬上變得寂靜,薛雲開夾菜的手也停在半空,連咀嚼的聲音也沒了。馬凱清也怔了怔,臉側向左寶貴,正提起酒杯的手也緩緩放下。
沈靜半晌,薛雲開終於忍不住,咽了壹口,嗤笑道:“如此兵單,怎能還分兵漢城?”
然而左寶貴還是壹臉嚴肅:“兵是不多,去不去漢城也可以再斟酌,但關鍵是,和倭人壹樣,先據守四周之險,使對方不能裕如赴平,咱後路的援兵就能相機前進。”
左寶貴說的其實也不是沒有想過,薛雲開慢慢地斂起那“笑容”,坐直了腰,臉色又冷起來,籲了口氣,凝思片刻,眼睛斜著桌子上的杯子說:“平壤與漢城相距千余裏,要是南下,必定難以通氣,且容易被倭人從中攔截,或繞過咱們出擊之師直取平壤。若處處留兵,咱前方和平壤之兵就更少了。”
左寶貴反駁道:“現在不是他們北上就是咱們南下,誰沒有通氣之虞?誰不怕被對方從中攔截或?何況中朝壹衣帶水,咱們後方援兵陸續繼至,反觀他們隔海而來,背水而戰,比咱們還艱難,隨帶糧食也必定不多,為何人家還敢銳意北上,而我等卻龜縮不前呢?”
“說起糧食……”本來壹時間也難以反駁,但最後聽見“糧食”,就馬上想到了。薛雲開擱下筷子,雙手放在桌上,看著眼前壹桌的飯菜,冷冷地笑了笑,但又像是苦笑:“這可又是壹大難處呀!咱們為求先進平壤,都是人先走,而糧草在後。但現在也快壹個月了,盛軍國內的糧草才剛到旅順,就算到了義州,也得像毅軍的糧草壹樣,不知何時才能過江,過了江的還要沿那條該死的朝鮮後路上轉運,目下咱們隨帶的軍糧還有在路上的呢!我想,貴軍也好不到哪去吧?”
見左寶貴默默地聽著,沒有回話,薛雲開繼續道:“目下平壤已近萬人,吃的都是隨身攜帶的那丁點的糧食,咱們雖已委托平安道就地籌措,但物價就隨之上漲。雖說朝鮮物價便宜,但平壤的百姓也得吃的呀!還未說即將到來的蘆榆防軍和各路援師?妳說,如此境況,如何南下?”
然而左寶貴卻好像早就想過這問題,盯著薛雲開道:“既然平壤是養不起這麽多人,那咱們就更應該分兵駐紮,此其壹。其二,現在開始秋收季節,而平壤漢城之間農田眾多,我想應該沒有糧食之虞。其三,我也說了,咱們南下不壹定要去漢城,只據守四周之險,最多出行數百裏,要是糧食遠在義州,那在黃州還是在平壤又有何區別?”
薛雲開反駁不了,細起眼睛看著左寶貴,眼冒寒光。老實說,薛雲開雖然縱情酒色,但習慣武人相輕的他絕不是泛泛之輩,而他亦有心再官升壹級,所以他此番被派來此地,絕不像那些盲目自大的官兵,相反,他早就聽說過日軍近年勤練西法,務求脫胎換骨,也早就想過眾多對策,這也是為何他老覺得兵力太單。
但他始終認為,以壹萬兵力死守平壤,靠著平壤的天險和雄偉的城墻,縱是惡戰,相信倭人亦難壹舉攻下。而時日壹長,也就如左寶貴所說,後方緩師陸續趕至,對倭人必然不利,那時候再南下漢城也不為遲。故在薛雲開看來,其他任何策略都得冒不必要的險。
但最重要的還是,作為北洋嫡系的他,早就收到壹意主和的李鴻章的指示,絕不能孟浪進兵。這和其海戰思維如出壹轍,重兵之駐平壤猶如水師之守渤海,兩者都只作“猛虎在山之勢”,務求以逸待勞。畢竟,盛軍、毅軍和北洋水師都是李鴻章的家當,打光了自己也完了。何況,所謂的四大軍已經是東拼西湊,壹時三刻也實在難以再擠出什麽援兵來。故即便薛雲開真覺得左寶貴的話有理,也絕不敢去改變李鴻章親自定下的策略。
至於左寶貴則已離開北洋多年,此次奉軍為四大軍之壹,也是由李鴻章出面請裕康而非直接調遣。故李鴻章其實是不太好意思對奉軍指手畫腳的,但同時也不會向其透露其心裏的盤算,當然這也可以免得左寶貴摻和。至於對李鴻章唯命是從的薛雲開,對於這個由上司請來的左寶貴,即便對他更不滿,也不好意思隨意拿上司的話來壓他。
故此刻的薛雲開也不想再反駁左寶貴,也沒心思去思量如何反駁,只道他欲爭功,又或是輕敵,緩緩道:“左軍門呀……妳有妳的道理,但妳說的,終究還是冒進。此次倭人來勢洶洶,有備而來,咱萬不可以輕敵,葉提督的捷報,未必可信。我看,咱們應該先固後路,後圖進取為妥。”
“我就是不輕敵才有此議,”左寶貴鼻子吭氣道:“至於葉提督的捷報,我壓根就不信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