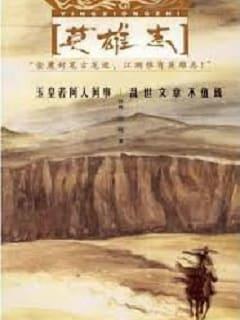- [ 免費 ] 楔子·壹
- [ 免費 ] 楔子·二
- [ 免費 ] 楔子
- [ 免費 ] 第壹章 鐵血伍捕頭
- [ 免費 ] 第二章 滅門血案
- [ 免費 ] 第三章 救命錦囊
- [ 免費 ] 第四章 昆侖劍出血汪洋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章 死與降
- [ 免費 ] 第六章 鐵劍震天南
- [ 免費 ] 第七章 顛沛流離
- [ 免費 ] 第八章 淚灑京城
- [ 免費 ] 第壹章 落第秀才
- [ 免費 ] 第二章 為天地立心
- [ 免費 ] 第三章 白水豈能度日
- [ 免費 ] 第四章 大富人家
- [ 免費 ] 第五章 無雙連拳
- [ 免費 ] 第六章 月上柳梢頭
- [ 免費 ] 第七章 夢碎揚州
- [ 免費 ] 第八章 天地壹沙鷗
- [ 免費 ] 第壹章 山東大鹵面
- [ 免費 ] 第二章 相逢何必曾相識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章 血戰紫禁城
- [ 免費 ] 第四章 風流司郎中
- [ 免費 ] 第五章 尚書府上
- [ 免費 ] 第六章 火貪壹刀
- [ 免費 ] 第七章 羊皮玄機
- [ 免費 ] 第八章 戰雲密布
- [ 免費 ] 第壹章 九華門人
- [ 免費 ] 第二章 蛇蠍女子
- [ 免費 ] 第三章 嵩山少林寺
- [ 免費 ] 第四章 武勇煞金
- [ 免費 ] 第五章 戊辰歲終
- [ 免費 ] 第六章 江東帆影
- [ 免費 ] 第七章 賭約
- [ 免費 ] 第八章 龍皇動世
- [ 免費 ] 第壹章 銀川公主
- [ 免費 ] 第二章 西出梁山第壹人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章 昭君出塞
- [ 免費 ] 第四章 天朝國威
- [ 免費 ] 第五章 西疆第壹武勇
- [ 免費 ] 第六章 忠義之心
- [ 免費 ] 第七章 天蒼蒼兮臨下土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章 明月出天山
- [ 免費 ] 第九章 大難不死
- [ 免費 ] 第十章 可汗大點兵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 勸君更盡壹杯酒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章 神胎寶血符天錄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章 玄關叩險
- [ 免費 ] 第三章 南天門
- [ 免費 ] 第四章 萬莫回頭
- [ 免費 ] 第五章 各顯神通
- [ 免費 ] 第六章 生死壹線
- [ 免費 ] 第七章 壹代真龍海中生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章 披羅紫氣
- [ 免費 ] 第九章 濃情蜜意
- [ 免費 ] 第十章 風雲將起
- [ 免費 ] 第壹章 笨孩子
- [ 免費 ] 第二章 長勝八百戰
- [ 免費 ] 第三章 天下群英會華山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章 真人不露相
- [ 免費 ] 第五章 封劍歸隱
- [ 免費 ] 第六章 天山傳人
- [ 免費 ] 第七章 制霸天下
- [ 免費 ] 第八章 比武奪帥
- [ 免費 ] 第九章 神劍如我
- [ 免費 ] 第十章 江山代有才人出 ...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 鐵口直斷
- [ 免費 ] 第壹章 歃血
- [ 免費 ] 第二章 人生不相見
- [ 免費 ] 第三章 最後壹戰
- [ 免費 ] 第四章 男兒漢
- [ 免費 ] 第五章 京華秋色
- [ 免費 ] 第六章 命裏有時終須有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章 打開天眼看文章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章 西角牌樓
- [ 免費 ] 第九章 決勝千裏
- [ 免費 ] 第十章 春風輕拂楊柳岸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章 三重懼
- [ 免費 ] 第二章 新官上任三把火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章 文淵閣
- [ 免費 ] 第四章 雷澤刑天
- [ 免費 ] 第五章 神劍降世
- [ 免費 ] 第六章 情愛
- [ 免費 ] 第七章 講和
- [ 免費 ] 第八章 八十三
- [ 免費 ] 第九章 城西鬼屋
- [ 免費 ] 第壹章 宦海前程
- [ 免費 ] 第二章 助漢則楚亡
- [ 免費 ] 第三章 煮酒論英雄
- [ 免費 ] 第四章 江海夜歸人
- [ 免費 ] 第五章 忠義孤臣枉癡心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章 縱使相逢應不識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章 兄弟
- [ 免費 ] 第八章 仗義多從屠狗輩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章 人生三寶
- [ 免費 ] 第十章 今夕復何夕
- [ 免費 ] 第壹章 爺爺生在天地間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章 風雨故人來
- [ 免費 ] 第三章 自古聖賢多寂寞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章 三十功名塵與土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章 當恨此身非我有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章 神女第三峰
- [ 免費 ] 第七章 我自橫刀向天笑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章 初出茅廬第壹功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章 狼煙再起
- [ 免費 ] 第壹章 大敵當前
- [ 免費 ] 第二章 初生之犢
- [ 免費 ] 第三章 修羅王
- [ 免費 ] 第四章 漁陽鼙鼓動地來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章 亂世兒女
- [ 免費 ] 第六章 智敵群雄
- [ 免費 ] 第七章 血戰通天塔
- [ 免費 ] 第八章 雙雄會
- [ 免費 ] 第九章 還君明珠
- [ 免費 ] 第十章 聖旨到
- [ 免費 ] 第壹章 天涯共此時
- [ 免費 ] 第二章 秦霸先
- [ 免費 ] 第三章 龍潛大海
- [ 免費 ] 第四章 大犄角
- [ 免費 ] 第五章 怒蒼山興兵雪恨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章 上少林
- [ 免費 ] 第七章 闖將
- [ 免費 ] 第八章 硬將
- [ 免費 ] 第九章 上將
- [ 免費 ] 第十章 鬼門開
- [ 免費 ] 第壹章 超世誌
- [ 免費 ] 第二章 人貴自知
- [ 免費 ] 第三章 天命如此
- [ 免費 ] 第四章 蕭墻之中
- [ 免費 ] 第五章 敗戰將不死
- [ 免費 ] 第六章 謝主隆恩
- [ 免費 ] 第七章 金水橋畔龍吐珠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章 壹切愛憎會
- [ 免費 ] 第九章 大輪回
- [ 免費 ] 第十章 投怒蒼
- [ 免費 ] 第壹章 大施主
- [ 免費 ] 第二章 萬夫莫敵
- [ 免費 ] 第三章 邀杯
- [ 免費 ] 第四章 共飲
- [ 免費 ] 第五章 東風吹醒英雄夢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章 最後的旅程
- [ 免費 ] 第七章 濁濁塵世
- [ 免費 ] 第八章 放逐
- [ 免費 ] 第九章 魁星戰五關
- [ 免費 ] 第十章 壹代新人換舊人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章 魔訊
- [ 免費 ] 第二章 智劍平八方
- [ 免費 ] 第三章 人間惡來
- [ 免費 ] 第四章 花滿池塘得自由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章 天外之人
- [ 免費 ] 第六章 永不服輸
- [ 免費 ] 第七章 黑契丹
- [ 免費 ] 第八章 千錘百煉出深山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章 魔域
- [ 免費 ] 第十章 十年壹覺
- [ 免費 ] 楔子
- [ 免費 ] 第壹章 英雄墳場
- [ 免費 ] 第二章 觀海雲遠
- [ 免費 ] 第三章 黑太子
- [ 免費 ] 第四章 京杭大河
- [ 免費 ] 第五章 怒者道之勤
- [ 免費 ] 第六章 修羅天之罰
- [ 免費 ] 第七章 如夢幻影
- [ 免費 ] 第八章 自願的逃犯
- [ 免費 ] 第九章 無解難題
- [ 免費 ] 第十章 回家
- [ 免費 ] 第壹章 皇天在上
- [ 免費 ] 第二章 奉天翊運推誠武臣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章 千裏姻緣壹線牽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章 小樓壹夜聽春曲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章 靈吾玄誌
- [ 免費 ] 第六章 壯士十年歸
- [ 免費 ] 第七章 天寒翠袖薄
- [ 免費 ] 第八章 舉案齊眉
- [ 免費 ] 第九章 冤家
- [ 免費 ] 第壹章 哀宗
- [ 免費 ] 第二章 人之初
- [ 免費 ] 第三章 章臺柳
- [ 免費 ] 第四章 天涯何處無芳草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章 天知地知
- [ 免費 ] 第六章 犧牲小我
- [ 免費 ] 第七章 閑來無事不從容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章 無名火
- [ 免費 ] 第九章 彩雲追月
- [ 免費 ] 第十章 開鑼
- [ 免費 ] 第壹章 怒峰頂上
- [ 免費 ] 第二章 大後方
- [ 免費 ] 第三章 天堂有路妳不走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章 地獄無門妳自來投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章 天訣
- [ 免費 ] 第六章 修羅本相
- [ 免費 ] 第七章 善穆義勇人
- [ 免費 ] 第八章 天機
- [ 免費 ] 第九章 大贏家
- [ 免費 ] 楔子
- [ 免費 ] 第壹章 正統軍
- [ 免費 ] 第二章 小水滴
- [ 免費 ] 第三章 兩顆石頭飛上天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章 老驥伏櫪
- [ 免費 ] 第五章 壹顆大石落了地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章 春郊試馬
- [ 免費 ] 第七章 木蘭原是尚書郎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章 父子
- [ 免費 ] 第九章 不識廬山真面目 ...
- [ 免費 ] 第十章 山中小景
- [ 免費 ] 第壹章 議和
- [ 免費 ] 第二章 天下第壹大氣力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章 天下第壹大笑話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章 新年新氣象
- [ 免費 ] 第五章 人生何處不相逢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章 北極峰
- [ 免費 ] 第七章 參與商
- [ 免費 ] 第八章 小泥鰍
- [ 免費 ] 第九章 天之歷數在爾躬 ...
- [ 免費 ] 第十章 吾皇萬歲萬萬歲 ...
杏書首頁 我的書架 A-AA+ 去發書評 收藏 書簽 手機
简
第三章 天下第壹大笑話
2018-8-30 14:27
天底下的人,很少沒有秘密。便算是清心寡欲的和尚,木魚裏往往也藏了幾分玄機。也因此,傅元影壹直是國丈最倚重的人。道理很明白,因為他能守口如瓶。哪怕再駭人聽聞的事情,壹旦傳入他的耳中,就不會再泄出壹字半句。
“守密”之難,非是發幾個毒誓就能了事,從埋藏秘密那壹日,傅元影不知經過了多少考驗,人情刺探、權勢脅迫、美色利誘,他全都熬過去了,這才平平安安過了二十四年。
可惜真能稱作秘密的東西,便不會隨時光而流逝,反會如壹壇好酒,越陳越烈。隨著正統皇帝登基,瓊家地位日高,傅元影心裏的秘密也越來越重,幾乎逼得他喘不過氣來。
“老爺子……”今早壹如往常,傅元影忙完了華山本門的事情,便又來向國丈請安。聽他輕輕敲門,低聲問道:“您起來了嗎?”
房裏並無聲息,也不知國丈是否起身了,傅元影無可奈何,只能轉望門邊的丫嬛,聽她們低聲埋怨:“老爺子方才發了好大的脾氣,見人便罵,咱們誰都不敢進去……”
傅元影點了點頭:“都下去吧,今兒我來服侍更衣。”侍女如得皇恩大赦,急急告退。傅元影也不多說了,把手按上門板,將房門壹推,霎時壹股藥味撲鼻而來,屋內昏暗陰森,滿是腐敗之氣,望來直如死人的陰宅。
老人家總是如此,再明亮的地方,再寬敞的所在,壹旦讓他們住下,總有法子鬧得死氣沈沈。不過這也不能怪瓊武川,八十多歲的人,手腳不便,體弱多病,夜裏睡不穩,白天不開心,活著便似受罪,好似不能讓全天下跟著難過,他們便稱不了心。
傅元影服侍國丈多年,自也明白老人家的脾氣,是以這十多年來,他每日為瓊武川做的第壹件事,便是替老國丈開窗透氣,多曬太陽,心情也能開朗些。他行入房中,正要推開窗扉,卻聽屋裏傳來老邁喘息:“別開……這樣挺好……”
老人家又作怪了,傅元影搖頭道:“老爺子,快要晌午了,您該起床啦。”
“雨楓,來……來……”國丈微微喘息:“我……我快不成了,快來,我……我有要緊話和妳說……”傅元影見慣這些伎倆了,便道:“老爺子起來更衣吧,有話壹會兒再說。”
“雨楓……來、過來……”老人家很是固執,催促幾聲,忽又猛烈嗆咳,自在床上呻吟,傅元影無可奈何,只得行將過來,替老人家倒來壹杯熱茶,讓他潤潤喉嚨。
“我老了……不中用了……”床上坐了壹名老者,雙頰凹陷,目光灰敗,正是皇後娘娘的老父,“英國公”瓊武川。他喝了口茶,低喘道:“雨楓、來……來……”
嘩地壹聲,傅元影趁機掀開簾幕,推窗透氣,霎時間天光地明,屋裏又多了勃勃生機,他提起水壺,倒了滿滿壹盆熱水,道:“老爺子洗臉吧。川王爺壹早就來了,等了您個把時辰。”
屋外光芒刺眼,瓊武川舉手遮目,喘道:“怎麽……阿郢那小子不耐煩了?”傅元影道:“這倒沒有。”
“那妳急什麽……”瓊武川咳嗽喘息:“是不是伍……伍定遠派人來了?”傅元影心下壹凜:“您知道了?”國丈喘道:“今早……今早嗩吶吹得老響……”掏了掏耳孔,露出嘴裏剩下的幾顆黃牙,咧嘴壹笑:“妳真當我耳背啦?”
餓鬼圍城,瓊武川早已知道了。傅元影也不多說什麽,便取來了毛巾,自替老爺子洗臉。
在娟兒那樣的小姑娘眼裏看來,瓊武川只是個糟老頭兒,不可理喻,其實傅元影心裏明白,國丈最善扮豬吃老虎,他精明似鬼,城府過人,滿面胡塗都是裝出來的。若非如此,當年他早與“江劉柳”三派壹同殞滅,何來的本錢與“威武文楊”同朝為臣?
瓊武川任憑傅元影擦臉,壹邊低聲來問:“伍定遠派了多少車來?”傅元影道:“壹共來了三十輛車,都是運糧的。另有五百名兵卒,全在府外候著,說是要護送老爺子過去紅螺寺。”
國丈道:“車子全是空的,對吧?”傅元影欠了欠身,道:“老爺子英明。”瓊武川點了點頭,低聲道:“有心人……伍定遠對我還是恭敬的……”
現今戰火將至,天下最平安的地方,自是京北紅螺寺,正統皇帝的行駕所在。只是瓊府是帝王姻親,洞見觀瞻,倘學別的臣子抱頭鼠竄,不說丟了瓊家自己的臉,怕連皇上也要顏面無光。正因如此,伍定遠才打著運糧的旗號,暗中將國丈送至紅螺寺,也好讓皇後娘娘壹家相會。
伍定遠是個周到的人,他自己並未將家人送出城外,卻暗中替國丈打點好了壹切。這說明他懂得朝廷的規矩,哪些事情該說壹套、哪些事情該做壹套,他心知肚明。
瓊武川洗過了臉,精神略振,便道:“芳兒呢?還在楊家麽?”傅元影深深吸了口氣,嘴中卻應了壹聲:“是。”國丈道:“妳打算什麽時候派人去接她?”傅元影躬身道:“此事雨楓不敢作主,還要請老爺子吩咐。”
“等我吩咐?”國丈嘿嘿笑道:“那妳又為何把穎超交給了玉瑛?這事怎又不必我吩咐啦?”
傅元影雙肩微動,沒敢作聲。瓊武川接過茶杯,漱了漱口,吐到了臉盆裏,道:“萬福樓這麽高,沒摔死他吧?”傅元影嘆道:“老爺子既然都知道了,又何必問我?”
瓊武川道:“雨楓,別介,我這只是試壹試妳……”說著從枕下取出物事,塞到傅元影手裏,道:“看看妳是不是真把我當糟老頭了?”傅元影低頭壹看,只見手裏多了塊鐵牌,篆刻雄鷹,雙翼全展,大書“鎮國鐵衛”四字。
“雨楓……妳知道的事,我全都知道……”瓊武川伸了個懶腰,哈欠道:“至於妳不知道的事呢……嘿嘿……”說著說,便又朝床沿拍了拍,道:“坐下,我有大事要交代妳。”
國丈連番催促,傅元影只得搬來壹張凳子,壹如往常坐在床邊,任憑國丈握住他的手。
瓊武川年輕時很高大,身長至少九尺,年老之後,個頭雖變矮了,那雙手卻還是壹樣大,他握緊了傅元影的手,忽道:“雨楓……妳這趟下去貴州,可曾打聽到不凡的下落了?”
傅元影別開了臉,低聲道:“老爺子忘了麽?您當年答應過娘娘什麽了?”
“玉瑛?”瓊武川睜開了眼,壹臉茫然:“我……我答應她什麽了?”
人老了,最大的好處便是這個,眼看國丈又裝成了老糊塗,傅元影也不想多說了,瓊武川笑道:“雨楓啊,別老是生悶氣……其實穎超這件事,妳處置得很對。”傅元影低聲道:“老爺子是說……我把他交給了娘娘?”瓊武川呵呵笑道:“是啊,穎超這孩子心太高了……他不是寧不凡……卻老想當寧不凡,妳得想法子殺殺他的銳氣,不然他不能死心塌地守著芳兒。”
傅元影默默聽著,忽道:“老爺子,穎超是壹個劍客。”國丈笑道:“妳呢?妳不也是個劍客?”傅元影默然半晌,似想說些什麽,卻又忍住了,瓊武川察言觀色,呵呵笑道:“雨楓啊,妳就不怕穎超會落到妳這個下稍嗎?”
傅元影搖了搖頭,道:“老爺子多心了。我華山門下,壹人壹把劍。穎超的劍與我、與他師父的都不同,他遲早會找到自己的路子。”瓊武川笑道:“什麽路?死路?”
瓊武川有很多面貌,在江充面前,他像個瞎子,跌跌撞撞,讓人懶得計較。在景泰皇帝跟前,他又像個傻子,天天打擺子,到了華山門人眼中,他卻又似個神算子,樣樣事都算無遺策,總之千變萬化、莫衷壹是,根本就是壹個戲子。
傅元影並未頂嘴,眼見桌上還擱著壹碗湯藥,便端了過來,道:“老爺子,吃藥吧。”
瓊武川張開了嘴,如小孩般讓人餵了壹湯匙,道:“雨楓啊,妳也別總是掛記著不凡、掛記著穎超,今兒咱倆便來說說妳的事吧。”傅元影皺眉道:“我?我有什麽好說的?”國丈笑道:“妳曉得妳像誰嗎?”
傅元影無心回話,提起湯勺,正要再餵,卻聽瓊武川道:“妳像楊肅觀。”
傅元影微微壹楞,手上湯匙微微壹晃,險些濺了出來。瓊武川握住他的手,微微摩挲,道:“雨楓啊,妳可知我為何把妳比成楊肅觀?”傅元影搖了搖頭,示意不知,瓊武川呵呵笑道:“妳可曉得朝廷若是少了伍定遠,會怎麽地?”傅元影道:“兵兇戰危,勢若危卵。”
瓊武川狡黠壹笑:“那咱們現下有了伍定遠,就不兵兇戰危,勢若危卵了嗎?”
國丈所言不錯,伍定遠早已受了朝廷重用,可前線如火、京師被圍,仍舊是天下大亂,說來伍定遠便似壹帖臭郎中的老藥,延得了命,卻斷不了根。傅元影推測話意,沈吟道:“那照老爺子的意思,咱們這朝廷若是少了楊大人……”
“即刻便要……”瓊武川握住那塊鐵牌,咬牙道:“覆亡。”話到嘴邊,突又猛烈嗆咳,湯藥都嘔了出來,傅元影忙沿國丈的背心撫了撫,咳嗽立緩,便又取出布巾,替他擦拭嘴角。
瓊武川淡淡幾句話,卻也點出了傅元影的身價。華山有了寧不凡,能夠威震天下,有了呂應裳,可以添光增彩,可沒了傅元影,華山卻有立即傾倒之虞。
“懂了吧,雨楓。”瓊武川喘過了氣,便又嘶啞道:“妳……才是華山真正的大掌櫃啊。”
傅元影默默聽著,忽道:“老爺子過獎了,雨楓沒這個本事。”瓊武川笑道:“別介啊、雨楓,妳可知瓊某活到了八十歲,靠的是什麽嗎?”傅元影道:“老爺子靠的是神機妙算。”瓊武川戟指笑罵:“違心之論。要說神機妙算,我哪算得過劉敬?”傅元影道:“那老爺子靠的是什麽?”
瓊武川嘿嘿笑道:“我善觀人身上的‘氣’。”傅元影蹙眉道:“氣?您指的內力,還是……”
瓊武川傲然道:“氣!就是霸氣、英氣、秀氣、才氣,還有吾善養的浩然正氣。”傅元影點了點頭,瞧向床邊那塊“鎮國鐵衛之令”,頷首道:“這個正氣,老爺子養的真是太充足了。”
“他媽的!”瓊武川把手壹揮,弄翻了茶碗,罵道:“都到了今天,妳還是反對我投入客棧嗎?”傅元影欠身道:“雨楓不敢,老爺子向來神機妙算,做事自有道哩,何勞旁人過問?”
瓊武川惱道:“是,咱們都是龜孫子,最沒出息……可雨楓啊,妳到底有沒想過,似我這般膽小之人……那年復辟大戰,卻為何把身家性命都賭在楊肅觀身上?”
眼看國丈打翻了湯碗,弄得滿身是藥,又臟又黏,傅元影只得壹邊替他擦拭,壹邊道:“老爺子很看重楊大人的幹才,對嗎?”瓊武川斜目冷笑:“笑話。當年他不過是個小小兵部郎中,與我素無深交,我哪知他有何幹才?”
傅元影微微壹凜,也知國丈這話說到要緊處了,當年劉敬舉事之時,手握東廠,連結內外,來勢洶洶,瓊武川卻躲得不見蹤影。到了楊肅觀決心復辟時,不僅早被開革為民,尚且無兵無權,聲勢全不能與劉敬相比。卻不知瓊武川何以拒絕了劉敬,卻選擇與楊肅觀連手?
瓊武川喘了口氣,慢慢掙紮起身:“很奇怪吧……劉敬和我是多年交情,可他舉事之時,我卻嚇得噤若寒蟬,好似成了壹只縮頭烏龜,就怕擔上幹系……”傅元影找了壹件幹凈內衫,隨口道:“老爺子,風險是娘娘擔著。要是出了事,砍的是她的頭,傷不到您壹根寒毛。”
瓊武川大怒道:“妳說什麽?”把內衫搶了過來,拋到了地下,暴吼道:“混蛋東西!昨晚芳兒罵我的那些話,妳都聽到了?”傅元影道:“老爺子,您方才不還說我像楊大人?怎麽這會兒又是混蛋了?”
“混蛋……”瓊武川眼中現出壹絲惱怒,壹拳便望傅元影身上打去。砰地壹聲,“雨楓先生”肩頭略沈,便卸下了氣力,隨即撿起地下的內衫,替國丈換上。
國丈像個孩子,打過了人,氣也消解了幾分,又道:“雨楓,說正格的,妳和楊大人熟麽?”傅元影道:“當朝五輔,天絕傳人,我是久仰大名了。”
瓊武川道:“妳第壹回見到他時,想到了什麽?”傅元影道:“面帶城府,語無真心。”瓊武川輕蔑壹笑:“那妳只看到了皮相。”傅元影哦了壹聲:“那老爺子看到了什麽?”瓊武川道:“我見到了他身上的‘氣’。”傅元影笑了笑:“老爺子是驚嘆於楊大人身上的‘秀氣’,是嗎?”
“放妳媽的屁!”瓊武川脫下了衣服,說話更粗了,大聲道:“秀氣?什麽秀氣?我女色尚且不愛,還愛什麽男色?”傅元影微笑道:“那倒是。老爺子清心寡欲,天下罕見。”
“譏諷我是吧?”瓊武川火大了,正要再次出拳打人,卻聽傅元影道:“老爺子,手舉高。”拉住了國丈的手,帶他穿過了袖子,瓊武川咒罵幾聲,任他替自己穿衣,嘴中卻吼道:“聽好了!瓊某生於永樂年間,經五朝四帝,看盡天下風流人物,卻沒壹個人能像楊肅觀那樣……”頓了頓,話聲轉為低沈:“生具南面之氣。”
子曰:“雍也可使南面”,南面之氣,亦即王者之氣也,傅元影微起錯愕,隨即搖了搖頭,釋然壹笑:“老爺子,雨楓倒不知您還善於看相。”
瓊武川搖頭道:“雨楓,妳不是官場中人,自不信讖緯的道理。可咱們這些朝廷裏打滾的,最信者三,壹是命、壹是運、壹是氣!幾十年下來,潮起潮落,教妳不信也難。”
傅元影不置可否,含笑又道:“那照老爺子看來,楊大人的面相有何特異之處?”瓊武川深深嘆了口氣,道:“記得是景泰三十三年吧……那年楊肅觀打了個敗仗,到了奉天門前,那時我也剛好路過,猛壹見到他,突然被他嚇了壹大跳,險些滑了壹大跤……”
傅元影皺眉道:“滑了壹跤?怎會如此?”瓊武川喘息道:“這我也說不上來,我只記得那天他背對著奉天門,凝望北京,那壹刻,我突然覺得似曾相識,便在心裏直喊,對!這就是南面之相……我見過的……”
傅元影越聽越是不解,皺眉道:“老爺子的意思是……那時的楊大人看起來很面熟麽?”
瓊武川低聲道:“這我說不清楚……反正那壹幕就是似曾相識,好像在哪兒見過……自那之後,我便知道他絕非池中之物,早晚能飛騰人間……”
這話玄之又玄,傅元影自然聽不懂,他推測半晌,忽道:“是了,這是因為他長得像他父親楊遠,所以站在奉天門前,猛壹下便讓您誤認了,是嗎?”瓊武川搖頭道:“不是。楊遠身上沒有他那種氣。”傅元影道:“您的意思是說,他父子倆長得不像?”
瓊武川道:“說不像,那也不算,這楊家父子都是白面斯文,也算有幾分神似。可不知為何,他老子就沒那個氣,不似他這大兒子楊肅觀,讓我越看越覺得膽戰心驚……”
傅元影越聽越胡塗,便道:“老爺子,我這樣問吧,您初見楊大人時,他那時多大歲數?”瓊武川道:“那年他剛從少林寺還俗,年方十八。”傅元影道:“那時您便覺得他有‘王氣’麽?”
瓊武川搖頭嘆道:“那時……那時還不覺得。”傅元影微微壹笑:“這麽說來,這王者之氣還是與時俱進的?”瓊武川聽得諷刺,卻也不去反駁,只低聲喃喃:“看來……真是如此。”
老人家總是老眼昏花,疑神疑鬼,傅元影忍不住笑著搖頭了:“那劉總管、柳昂天呢?他倆見了楊肅觀,也覺得此人似曾相識嗎?”瓊武川搖頭道:“沒聽說過。”傅元影道:“那江充呢?聽說這江太師是真正懂得面相的,他也沒看出楊肅觀非比尋常?”
瓊武川木然道:“沒看出。所以他才成了我的……”突然嘿嘿壹笑,道:“手下敗將。”
景泰三雄之中,向以江充城府最深、劉敬智慧最高,柳昂天識人最廣,想這“江劉柳”三大權臣都瞧不出的事情,瓊武川卻能慧眼獨具,不能不讓傅元影半信半疑。眼看傅元影沒說話了,瓊武川低聲道:“雨楓,妳當我發瘋了,是嗎?”
傅元影搖頭道:“不,老爺子沒瘋,瘋的是我。”瓊武川惱道:“什麽意思?”傅元影淡淡地道:“老爺子是贏家。贏家是不會瘋的。”
確實如此,十年前復辟大決戰,江劉柳都死了,瓊武川卻活了下來,這是因為他站對了邊,靠對了人,從此躍居為朝廷第壹世家,無可動搖。不過傅元影卻不知道,原來當年國丈選擇了楊肅觀,竟是因為此人的面相。
“衛青不敗由天幸,李廣無功緣數奇”,人生許多事,往往莫名其妙,這就叫天命。傅元影也不想追問了,伸手拉住國丈的褲帶,將他的睡褲拉了下來。瓊武川道:“雨楓,妳別當我是老糊塗,告訴妳,我瓊武川為人做事,向來是有遠見的,好比說……好比說……”傅元影接口道:“出手打跑自己的孫女?”
“他媽的是!”瓊武川用力壹拳捶在床上,吼道:“存心氣我是吧?混蛋……妳說!說!我為啥要打芳兒?”國丈氣得結巴,傅元影卻是面不改色:“老爺子是怕那姓盧的,是麽?”
瓊武川喘道:“看妳跟了我這許多年,總算還不胡塗啊……”伸手搭住傅元影的肩頭,提腿進了褲腳,咬牙道:“妳……妳曉得那姓盧的像誰?”先前國丈才說楊肅觀身有王者之氣,現下又替那姓盧的看起相了,傅元影替他綁好了褲帶,便又取來外衣,道:“老爺子,手舉高。”
國丈微微喘氣,慢慢穿上了袖子,道:“那姓盧的,讓我……讓我想到了我兒子……”
傅元影聞言壹怔,停手下來,只見國丈撫面低喘:“雨楓,妳說……為何瓊翊樣樣都強過我,卻會比我早死?”傅元影無言以對,正要帶著國丈穿衣,卻聽壹聲哽咽:“因為他這個人……比誰都有良心……”話到嘴邊,突然激動起來:“所以他……註定要第壹個倒下!”
砰地壹聲,國丈把腳壹踢,猛聽轟然巨響,木桌飛了起來,撞破窗扉,直直墜到了樓下。屋外響起壹片驚喊:“怎麽了?”傅元影大聲道:“沒事!這兒有我!”
瓊武川雖然年老多病,可發起威來,氣力仍是駭人,看他須發淩亂,抄起了桌上鋼鞭,使勁壹掃,乓瑯壹聲,先將衣櫃掃得坍了,隨即反手壹抽,又將花瓶盡數砸破,傅元影也不勸阻,只退到了墻邊,靜靜看著老人家發泄。
良久良久,國丈放落了鋼鞭,雙肩不住抽動,竟似哭出了聲。傅元影替他穿上外衣,低聲道:“老爺子別這樣了。當年翊少爺他……是自願喝下那杯酒的。”驟然之間,老國丈仰起頭來,熱淚卻從眼角滑落,哽咽道:“雨楓,妳……妳也覺得我是個心狠手辣的父親麽?”
傅元影低聲道:“老爺子,這話該問您的壹雙兒女,不能問我。”嘆了口氣,便從衣架上提起朝袍,徑自披到瓊武川的肩上。
這件官袍色呈艷紅,雙肩繡以獅虎,正中補子則是壹只五彩火鳳,看瓊武川官袍加身,不知怎地,原本氣息短促,卻變得呼吸剛猛,原本須發淩亂,卻成了豪邁落拓,他不再是什麽糟老頭,而是本朝右柱國、復辟大戰第壹大特功,“奉天翊運推誠武臣”,瓊武川。
忙了半個時辰,國丈總算穿戴完畢,傅元影擦了擦汗,道:“老爺子,可以走了麽?”瓊武川左手叉腰,右手提著鋼鞭,靜靜地道:“妳坐下。”
人要衣裝、佛要金裝,天下最大的靈丹妙藥,就是這壹帖。瓊武川穿上了官袍,說話也威嚴了許多,眼看傅元影乖乖就範,便道:“我這兒有件大事,攸關我瓊家滿門生死,得立時與妳商量。”傅元影心下壹凜:“老爺子說的是怒蒼……”
國丈制住了說話:“錯了。什麽怒蒼之禍、八王之亂,都要不了妳我的性命,真正能見生死的事,是這壹件。”說話之間,便從枕頭下取出壹張字紙,塞到“雨楓先生”手裏。傅元影微微壹奇,正要開掌來看,瓊武川卻道:“先別忙。”
國丈目光深沈,傅元影卻是心下迷惑,看現今朝廷兩件大案,壹是立儲案,也就是是國丈嘴裏的“八王之亂”,再壹個便是“怒蒼之禍”,西郊阜城門外的那把怒火,前者包圍群臣、後者包圍京城,都是迫在眉睫的大事,可國丈卻似心有旁騖?
屋裏靜悄悄的,只見國丈握住傅元影的手,嗓音轉為柔和,低聲道:“雨楓,妳今年多大歲數了?”傅元影欠身道:“過了元宵,雨楓就五十了。”瓊武川伸手出來,輕撫他的面頰,低聲道:“這麽說來,那個秘密……妳也守了二十四年了?”不知不覺間,傅元影身上發起抖來了,寒聲道:“老爺子,妳…妳這話是……”國丈低聲道:“那杯毒酒又來了。”
砰地壹聲,傅元影竟爾滑倒在地,張嘴駭然,瓊武川輕聲道:“打開紙團。”傅元影大口喘息,勉強撐起身子,只見掌心裏有張字紙,已讓國丈揉成了壹團,他慢慢將之展開,卻見到了壹行字,見是:“天下第壹大笑話”。
傅元影顫聲道:“這……這是……”瓊武川道:“猜吧,天下第壹大笑話是什麽?”
傅元影臉色鐵青,慢慢將字條翻到背面,看到了壹行字跡,見是:“皇後娘娘的兒子……”
“不姓朱”。
“啊呀!”陡見這心裏埋藏二十年的秘密,饒那傅元影練了壹輩子的內功,還是忍不住雙手抱頭,狂叫出來,正要將紙條撕得稀爛,卻聽國丈道:“定下神來,什麽都別動。”
傅元影低頭喘息,咬牙切齒,又聽國丈附耳道:“把字條收好,咱們還得靠它指引,揪出幕後主使。”聽得提醒,傅元影啊了壹聲,這才想起這字條是個線索,他將字條貼肉藏好,深深吸了口氣,語音顫抖:“老爺子,這……這字條是打哪來的?”
瓊武川替他斟了杯熱茶,道:“喝下去,先定定神再說。”傅元影坐了下來,慢慢喝了幾口熱茶,讓心情定下,聽得國丈低聲道:“我壹早起床,見到案上壓了這張字條,拿起壹看,才知出了大事。”
傅元影咬牙切齒:“有內奸,我……我既刻召人來問。”正要轉身離房,卻又讓瓊武川拉住了:“不要節外生枝。這不是府裏人送進來的。”傅元影嘶啞道:“何……何以見得?”
瓊武川靜靜地道:“只要是我瓊家的人,哪怕是壹條狗、壹只雞,都會受這字條牽連。誰會傻到拿自己全家的性命玩笑?”
姜是老的辣,這張字條若是泄漏出去,那便是罪夷九族的大罪。瓊府上下兩百余口人,無壹人能脫身。國丈不愧經歷過兩次復辟政變,生死關頭,拿捏精準。反倒是傅元影方寸大亂,喘了口氣,低聲又問:“那……那照老爺子看,這字條是什麽人送進來的?”
瓊武川道:“我推算過,此事只有兩個可能。其壹,便是立儲案。”傅元影心下壹醒,忙道:“徽唐徐豐魯?”瓊武川道:“正是。現今立儲在即,這些籓王兔崽子早在抓我瓊家的把柄,掘地三尺,無所不用其極,這便讓他們查出了蛛絲馬跡。那也未可知。”
傅元影聽著聽,忽道:“不會。”這回輪瓊武川“哦”了壹聲:“何以見得?”傅元影道:“老爺子,世上的秘密只消經過我的手,便不會再外泄。”傅元影這話說得斬釘截鐵,斷斷無轉圜余地了,料來“徽唐徐豐魯”便把瓊家的祖墳都掘開了,也挖不出這字條上的秘密,此間事情,必是他人所為。
“喀……嗨……”瓊武川推開窗扉,朝外吐了壹口膿痰。傅元影又道:“老爺子方才說了兩個可能,另壹個是什麽?”瓊武川提起茶碗,漱了漱口,道:“義勇人。”
“義……義勇人?”傅元影面色微變,瓊武川皺眉道:“怎麽?妳也聽過他們?”傅元影低聲道:“我……我曾聽若林提過幾次,說朝廷裏有壹幫人專和楊大人作對,好似叫‘反楊十大臣’,也不知是真是假。”瓊武川嘿嘿壹笑:“好妳個呂若林,明察秋毫啊……”
傅元影不願拉師兄下水,便轉過了話頭,道:“老爺子,您和這‘義勇人’有仇麽?”瓊武川道:“我是楊肅觀的盟友,這義勇人卻是楊大人的死敵,妳說咱們倆家有仇沒仇?”
傅元影低聲道:“這些人到底是什麽來歷?何以這般憎恨楊大人?”瓊武川道:“這些人有的是朝中大臣,有的是江湖術士,全都吃過楊肅觀的虧,於是便以柳昂天的名頭為號召,結盟立誓。”傅元影納悶道:“柳昂天?這人不是過世了?為何要以他為號召?”瓊武川道:“相傳柳昂天……死於楊肅觀之手……”傅元影心下壹凜,立時默然低頭,不再多問了。
守密之難,難如登天,想傅元影的肚子早被秘密裝得滿了,如何還裝得下新東西?聽得秘密又來了,忙掉過話頭,低聲道:“老爺子,倘使這字條真是義勇人搞的鬼……那他們是要……”
瓊武川附耳道:“他們是要我背叛‘鎮國鐵衛’,下手扳倒楊大人。”
傅元影心頭大震:“那……那要是老爺子不從呢?”瓊武川道:“這張字條便會放到萬歲爺的案上,妳想咱們瓊家會如何?”這話如同雷霆閃電,直打得“雨楓先生”作聲不得。良久良久,聽他低聲道:“老爺子,妳想過向楊大人求援嗎?”
瓊武川道:“這事若讓楊大人知道,我瓊家立時便倒。”傅元影聞言壹楞:“老爺子,妳……妳不也是鎮國鐵衛的……”瓊武川嘿嘿壹笑:“雨楓,妳還是沒弄懂啊,妳可知義勇人的靠山是什麽人?”傅元影沈吟道:“是……是宰輔何大人?還是……伍大都督?”
瓊武川搖頭道:“錯了,是皇上。”傅元影霍地起身,顫聲道:“皇上?”瓊武川淡淡地道:“妳可知皇上怎麽稱呼楊肅觀?”他笑了笑,自知傅元影猜不出,便道:“楊黨。”
眼看傅元影呼吸加促,瓊武川便嘆了口氣,道:“當年復辟政變之後,皇上立時察覺朝廷藏了所謂的‘楊黨’,遍布朝野。妳且想想,皇上好容易才拿回了大權,卻又聽說朝廷裏另有黨派集結,他會怎麽想?”傅元影低聲道:“日夜憂懼。”瓊武川木然道:“妳說對了。”
史記韓信傳有言:“狡兔死、走狗烹;飛鳥盡、良弓藏”,臥榻之旁,豈容有人鼾睡?依此觀之,楊肅觀其實形勢危殆,絕非外人想象得那般大權在握。
傅元影低聲道:“老爺子……皇上為何會隱忍楊大人至今?”國丈道:“怒蒼山。”
傅元影啊了壹聲,卻也聽懂了。正所謂飛鳥不盡、良弓不藏,只要秦仲海未倒,皇上便不會和楊肅觀撕破臉。傅元影點了點頭,低聲道:“難怪老爺子會說‘義勇人’的靠山便是皇上。原來藏著這壹層道理。”
瓊武川道:“沒錯,皇上不能沒有楊肅觀,卻又信不過楊肅觀,為了壓制楊黨的勢力,皇上對反楊大臣總是恩寵有佳,若非如此,那年馬人傑把皇上罵得壹文不值,如何能留下壹條命?”
“馬人傑?”傅元影皺眉道:“他……他也是反楊大臣?”國丈道:“客棧裏有句話,叫做‘俊傑萬山風’。妳猜猜,這個‘傑’字指的是誰?”傅元影低聲道:“便是馬人傑?”
國丈道:“就是他。反楊十大臣,善穆義勇人,這‘俊傑萬山風’裏的‘風’字,正是柳昂天的兒子柳雲風,‘萬’字則是現任都察院的大頭兒萬吉祥。上頭那個‘俊’字,則是內閣輔臣牟俊逸,妳別看馬人傑官大,論資排輩,還只能排到了第七。”
聽得朝廷重臣雲集,專以反楊為己任,傅元影自也暗暗心驚,忙道:“除了這五人,另外還有誰?”國丈道:“頭牌五位,至今尚未現身。客棧雖說到處刺探,至今也還是沒個定論。”傅元影低聲道:“這些人從不露面,彼此怎麽聯系?”
國丈道:“這就不清楚了。每回朝堂上要與楊黨爭執,多由牟俊逸、馬人傑他們發動,不過除開‘反楊’這門功課,這些大臣平日多半自行其是,就拿這餓鬼東渡的事來說,牟俊逸主戰、馬人傑主和,兩人便各執壹詞,公開對著幹了。”
傅元影對朝政不甚關心,心裏只掛記著字條,又道:“那照老爺子看來,義勇人的大首領究竟是什麽人?”國丈嘆了口氣,道:“此人神出鬼沒,仿佛有百變之身。我幾次差人跟蹤馬人傑,他卻都能及時脫身,至今仍是壹無所獲。”
傅元影微微壹凜:“老爺子派人跟蹤過馬大人?我怎麽不知情?”國丈淡淡地道:“妳們華山玉清是名門正派,有些事情不好出面。我便沒通知妳。”
傅元影咳嗽壹聲。自知國丈私下還養了壹批探子。白日裏的事情,多由華山門下代勞,夜裏的事情,則交由這批密探來幹。雖說武功比不上華山的大劍客們,下手卻狠辣了許多。
傅元影默默聽著,忽道:“老爺子,皇上知道您也是‘楊黨’嗎?”瓊武川嘿嘿壹笑:“妳說呢?皇上知不知道?”傅元影心下壹凜,忙道:“皇上……皇上已經知道了?”
瓊武川裂嘴壹笑:“知道?豈止是知道?那年楊肅觀挨了壹槍,從永定河裏爬了出來,妳曉得他第壹個找的是誰?就是我瓊武川!妳可知那時他渾身浴血、命在旦夕,卻拉著我去見了誰?見的就是皇上!那時瓊某賭上了身家性命,與楊肅觀歃血為盟,又是誰拉著咱倆的手,感激涕零、自稱永世不忘今日之恩?告訴妳,那個人便是咱們今日的……”提起鋼鞭壹砸,厲聲道:“皇上!”
楊黨、楊黨,昨日之舊愛,轉眼成今日之大患,傅元影默然半晌,低聲道:“老爺子這場富貴,來得著實不易。”國丈仰起頭來,怔怔嘆了口氣:“來得實在是……太難太難了……”
屋裏靜了下來,傅元影與瓊武川對望壹眼,兩人各自想著自己的心事,誰也沒作聲。
良久良久,聽得傅元影道:“老爺子,皇上想過要拔掉妳麽?”瓊武川道:“那還不至於。我手裏有張保命符,只消這張符還靈驗,我就不會有事。”傅元影道:“您說得是娘娘。”
瓊武川道:“沒錯,就是玉瑛。楊肅觀是有遠見的人,當年他拉攏我,其實為的就是這條裙帶。只消玉瑛還在,他與皇上之間便有個緩頰,可掉句話來說,要是這條裙帶汙了臟了……”聲音漸漸低緩,嘆道:“妳想他會怎麽做?”傅元影道:“他會壯士斷腕。”
瓊武川木然道:“妳說對了。依我推算,楊肅觀壹旦得知消息,非但不會替我等遮掩,反會率先揭發此事,否則他若受我瓊家所累,怕也要跟著壹齊倒了。”
前有狼、後有虎,這兒是九五至尊,正統皇帝,那兒卻是復辟奸雄,“鎮國鐵衛”的大掌櫃,無論向哪方開戰,都是死路壹條。如今腹背受敵,國丈卻連客棧的密探也不能用了,說來“紫雲軒”上下別無依靠,只能看華山高手的作為。
華山門人不少,堪用的大材卻不多,先看蘇穎超渾渾噩噩,再看瓊芳少女驕狂,耍耍威風可以,謀劃大事則遠遠不行,推來算去,只剩下大師兄呂應裳可以援手。只是這“若林先生”總是聰明得過了頭,壹旦察覺大事不妙,只怕腳底抹油,又要跑得不見蹤影了。
傅元影嘆了口氣,緩緩提起自己的佩劍,道:“老爺子希望我怎麽做?”
瓊武川道:“倘這字條是八王所為,咱們便有著力之處。畢竟‘徽唐徐豐魯’所求只在東宮,不會把咱們望死路上送,可若是義勇人所為,事情便難善了。”
傅元影垂首無語,國丈也是撫面沈思,良久良久,聽得老人家低聲道:“芳兒還在楊家,對嗎?”傅元影道:“是。”瓊武川道:“那好。妳這兩日先別急著接她回來,先把她留在楊府,若真出事了,也好扯楊肅觀下水。至於義勇人那邊……”喘氣半晌,道:“妳替我去找馬人傑,探探他的口風。”
傅元影忙道:“老爺子,馬大人是兵部尚書,咱們若是用強……”瓊武川道:“沒人要妳用強。馬人傑雖是義勇人,卻也是個明白人,當今怒蒼兵臨城下,大禍在前,他絕不會坐視咱們瓊家在此刻垮臺。”傅元影忙道:“萬壹……萬壹馬大人不願幫這個忙,那咱們……”
瓊武川道:“那也沒什麽,真到了絕路上,瓊某便打開西郊阜城門,恭迎怒王進京。”
轟地壹聲,傅元影腦中壹片空白,耳中更是嗡嗡作響,竟連話也說不出來了。
餓鬼圍城,人心惶惶,看國丈雖是皇帝親家,卻也生出了反心,何況其它?眼看傅元影臉色鐵青,瓊武川便又道:“雨楓,兵兇戰危,沒人是忠臣,也沒人是奸臣,大家都只求個滿門保全、全身而退。他們若逼急了我,姓瓊的只有反。”
對面是楊肅觀,背後是義勇人,頭上還有個正統皇帝,三方包夾,國丈的出路無他,恐怕真是在阜城門了,傅元影怔怔望著窗外,又聽國丈道:“好了,事不宜遲,妳趕緊吩咐家人收拾收拾,說咱們今夜要在紅螺寺裏掛單,絕不能讓皇上起了疑心。”
傅元影低聲答應了,正要轉身離開,卻聽國丈道:“且慢,我還有件事問妳。”傅元影躬身道:“老爺子請吩咐。”國丈撐起了身子,慢慢來到傅元影身邊,搭住了他的肩頭,壓低嗓子,嘶啞地道:“雨楓,那個孩子……”傅元影極深極深的吸了口氣,聽得瓊武川附耳道:“妳到底藏在什麽地方?”
傅元影低頭沈默,並未言語。國丈皺眉道:“都二十多年了,妳還信不過我?”
傅元影道:“老爺子,我答應過翊少爺了。這事不能說。”瓊武川搖頭嘆氣:“妳想得太多了,虎毒不噬子,我還能害了自己的外孫麽?我只想問問妳,那孩子平安麽?”
傅元影道:“老爺子放心,這二十多年來,雨楓壹直照看著他。”瓊武川雙眉壹軒,道:“壹直?”傅元影看似目光望地,實則雙眼圓睜,眉毛更吊了起來,國丈察言觀色,立時猛烈咳嗽,喘道:“那就好……那就好……有妳照看著……那我也放心了……”
傅元影躬身行禮,便又走下樓去,木板嘎滋嘎滋地響了起來,漸漸遠去。國丈把耳朵貼在墻上,傾聽良久,確信傅元影走遠了,方才道:“招度羅。”
喊聲壹出,屋梁上忽然垂下壹條繩索,降臨了壹道黑影,行到國丈面前,躬身道:“三當家。”瓊武川道:“方才我和傅雨楓的對答,妳都聽到了?”那黑影道:“聽到了。”瓊武川道:“很好,我現下有個差事給妳,知道是什麽嗎?”
黑影道:“三當家要找那個孩子。”瓊武川木然道:“妳說對了。那孩子理應躲在華山門下,算來已有二十四歲,姓啥名誰不知道、樣貌如何也不清楚,但有件事錯不了……”
黑影道:“資質,是嗎?”瓊武川道:“沒錯。蘇穎超成不了大器,華山絕學卻不能失傳。我要妳順著‘三達劍譜’去找,看看傅元影把‘三達劍’交給了誰,懂得這個意思嗎?”
那黑影道:“小人懂得。等找到那孩子以後,國丈是要……”瓊武川深深吸了口氣:“這我自有處置。”那黑影默然半晌,並不做聲,瓊武川惱道:“怎麽?信不過我?”
黑影道:“小人不敢。”他拉住了繩索,正要回到梁上,忽又頓了頓,道:“三當家,您方才說要迎怒蒼入京,該是玩笑話吧?”瓊武川道:“那是說給下面人聽的。妳要不放心,不妨把這話轉給大掌櫃。”那黑影道:“小人不敢。”
瓊武川道:“去吧,記得告訴大掌櫃,瓊某人的麻煩,瓊某自個兒收拾,絕不讓他操心。”
黑影拱手致意,身子慢慢飄了起來,順延繩索,回到了梁上。瓊武川立時爬起身來,動作迅捷之至,壹時貼耳在墻,確信黑影離去了,方才罵道:“壹群混蛋!”
木階嘎嘎作響,瓊武川推開了窗扉,朝窗外吐了口痰,便也拾級而下,離開了精舍。
幾十年來,國丈住的地方都沒變,壹直在紫雲軒的“碧濤樓”,此地壹來鄰近竹林,綠影碧濤,最能陶冶性情,二來地勢高,不但可瞧見瓊府的家廟議事廳,還能望見少閣主的臥房,紫雲軒的過去、未來,乃至於當下,無不在掌握之中。
天色嚴寒,慢慢又飄起了雪,也不知過了多久,園林裏奔來了壹人,喊道:“傅師叔!傅師叔!您在這兒嗎?”來人年紀頗輕,腰上帶劍,正是華山弟子施得興,來到了精舍下,不由愕然道:“師叔,您……您怎麽坐在這兒?”
園林裏盤膝正坐壹人,正是傅元影,看他滿頭霜雪寒花,不知在這兒待了多久。
碧濤樓可見過去、可見未來,卻見不到腳下。傅元影未曾躲藏,他只是靜靜坐著,國丈與招度羅來來去去,都沒發覺他,因為他是寧不凡的師弟,華山那套藏氣功夫,他也練了四十年。
傅元影盤膝而坐,將長劍平放腿上,不發壹語,施得興低聲道:“師叔,您……您還好麽?”
傅元影撫挲劍身,默然良久,方才道:“找我有事?”施得興見他神氣古怪,心裏有些害怕,低聲道:“外頭……外頭來了個太監,說晚間八世子要比武了,要咱們趕緊挑個大伴習出來,他好把名單送進宮裏。”傅元影皺眉道:“什麽大伴習?這是什麽名堂?”
施得興低聲道:“這……這弟子也不大清楚,好像是陪世子練武的伴當,那太監說……說這人選挺要緊的。趙五師祖找不到呂師伯,便要弟子來精舍找您,說要商量這個人選。”
傅元影緩緩站起身來,忽道:“陳得福呢?見到他了麽?”施得興嘆道:“那小子不知又發了什麽瘋,壹早便哭哭啼啼,躲在後廚不出來,說自己闖了大禍……”
傅元影點了點頭,握住了劍柄,“嗡”地壹聲大響,劍身已然出鞘,那弟子嚇了壹跳:“師叔,您……您怎麽了?”
“沒什麽……”當地壹聲,傅元影伸指在劍刃上壹彈,長劍前後擺蕩,發出了嗡嗡低響,聽他道:“只是看這柄劍藏了這麽多年……”說著從懷裏取出幹布,在劍上擦了擦,淡淡地道:“也該是擦亮它的時候了。”
“守密”之難,非是發幾個毒誓就能了事,從埋藏秘密那壹日,傅元影不知經過了多少考驗,人情刺探、權勢脅迫、美色利誘,他全都熬過去了,這才平平安安過了二十四年。
可惜真能稱作秘密的東西,便不會隨時光而流逝,反會如壹壇好酒,越陳越烈。隨著正統皇帝登基,瓊家地位日高,傅元影心裏的秘密也越來越重,幾乎逼得他喘不過氣來。
“老爺子……”今早壹如往常,傅元影忙完了華山本門的事情,便又來向國丈請安。聽他輕輕敲門,低聲問道:“您起來了嗎?”
房裏並無聲息,也不知國丈是否起身了,傅元影無可奈何,只能轉望門邊的丫嬛,聽她們低聲埋怨:“老爺子方才發了好大的脾氣,見人便罵,咱們誰都不敢進去……”
傅元影點了點頭:“都下去吧,今兒我來服侍更衣。”侍女如得皇恩大赦,急急告退。傅元影也不多說了,把手按上門板,將房門壹推,霎時壹股藥味撲鼻而來,屋內昏暗陰森,滿是腐敗之氣,望來直如死人的陰宅。
老人家總是如此,再明亮的地方,再寬敞的所在,壹旦讓他們住下,總有法子鬧得死氣沈沈。不過這也不能怪瓊武川,八十多歲的人,手腳不便,體弱多病,夜裏睡不穩,白天不開心,活著便似受罪,好似不能讓全天下跟著難過,他們便稱不了心。
傅元影服侍國丈多年,自也明白老人家的脾氣,是以這十多年來,他每日為瓊武川做的第壹件事,便是替老國丈開窗透氣,多曬太陽,心情也能開朗些。他行入房中,正要推開窗扉,卻聽屋裏傳來老邁喘息:“別開……這樣挺好……”
老人家又作怪了,傅元影搖頭道:“老爺子,快要晌午了,您該起床啦。”
“雨楓,來……來……”國丈微微喘息:“我……我快不成了,快來,我……我有要緊話和妳說……”傅元影見慣這些伎倆了,便道:“老爺子起來更衣吧,有話壹會兒再說。”
“雨楓……來、過來……”老人家很是固執,催促幾聲,忽又猛烈嗆咳,自在床上呻吟,傅元影無可奈何,只得行將過來,替老人家倒來壹杯熱茶,讓他潤潤喉嚨。
“我老了……不中用了……”床上坐了壹名老者,雙頰凹陷,目光灰敗,正是皇後娘娘的老父,“英國公”瓊武川。他喝了口茶,低喘道:“雨楓、來……來……”
嘩地壹聲,傅元影趁機掀開簾幕,推窗透氣,霎時間天光地明,屋裏又多了勃勃生機,他提起水壺,倒了滿滿壹盆熱水,道:“老爺子洗臉吧。川王爺壹早就來了,等了您個把時辰。”
屋外光芒刺眼,瓊武川舉手遮目,喘道:“怎麽……阿郢那小子不耐煩了?”傅元影道:“這倒沒有。”
“那妳急什麽……”瓊武川咳嗽喘息:“是不是伍……伍定遠派人來了?”傅元影心下壹凜:“您知道了?”國丈喘道:“今早……今早嗩吶吹得老響……”掏了掏耳孔,露出嘴裏剩下的幾顆黃牙,咧嘴壹笑:“妳真當我耳背啦?”
餓鬼圍城,瓊武川早已知道了。傅元影也不多說什麽,便取來了毛巾,自替老爺子洗臉。
在娟兒那樣的小姑娘眼裏看來,瓊武川只是個糟老頭兒,不可理喻,其實傅元影心裏明白,國丈最善扮豬吃老虎,他精明似鬼,城府過人,滿面胡塗都是裝出來的。若非如此,當年他早與“江劉柳”三派壹同殞滅,何來的本錢與“威武文楊”同朝為臣?
瓊武川任憑傅元影擦臉,壹邊低聲來問:“伍定遠派了多少車來?”傅元影道:“壹共來了三十輛車,都是運糧的。另有五百名兵卒,全在府外候著,說是要護送老爺子過去紅螺寺。”
國丈道:“車子全是空的,對吧?”傅元影欠了欠身,道:“老爺子英明。”瓊武川點了點頭,低聲道:“有心人……伍定遠對我還是恭敬的……”
現今戰火將至,天下最平安的地方,自是京北紅螺寺,正統皇帝的行駕所在。只是瓊府是帝王姻親,洞見觀瞻,倘學別的臣子抱頭鼠竄,不說丟了瓊家自己的臉,怕連皇上也要顏面無光。正因如此,伍定遠才打著運糧的旗號,暗中將國丈送至紅螺寺,也好讓皇後娘娘壹家相會。
伍定遠是個周到的人,他自己並未將家人送出城外,卻暗中替國丈打點好了壹切。這說明他懂得朝廷的規矩,哪些事情該說壹套、哪些事情該做壹套,他心知肚明。
瓊武川洗過了臉,精神略振,便道:“芳兒呢?還在楊家麽?”傅元影深深吸了口氣,嘴中卻應了壹聲:“是。”國丈道:“妳打算什麽時候派人去接她?”傅元影躬身道:“此事雨楓不敢作主,還要請老爺子吩咐。”
“等我吩咐?”國丈嘿嘿笑道:“那妳又為何把穎超交給了玉瑛?這事怎又不必我吩咐啦?”
傅元影雙肩微動,沒敢作聲。瓊武川接過茶杯,漱了漱口,吐到了臉盆裏,道:“萬福樓這麽高,沒摔死他吧?”傅元影嘆道:“老爺子既然都知道了,又何必問我?”
瓊武川道:“雨楓,別介,我這只是試壹試妳……”說著從枕下取出物事,塞到傅元影手裏,道:“看看妳是不是真把我當糟老頭了?”傅元影低頭壹看,只見手裏多了塊鐵牌,篆刻雄鷹,雙翼全展,大書“鎮國鐵衛”四字。
“雨楓……妳知道的事,我全都知道……”瓊武川伸了個懶腰,哈欠道:“至於妳不知道的事呢……嘿嘿……”說著說,便又朝床沿拍了拍,道:“坐下,我有大事要交代妳。”
國丈連番催促,傅元影只得搬來壹張凳子,壹如往常坐在床邊,任憑國丈握住他的手。
瓊武川年輕時很高大,身長至少九尺,年老之後,個頭雖變矮了,那雙手卻還是壹樣大,他握緊了傅元影的手,忽道:“雨楓……妳這趟下去貴州,可曾打聽到不凡的下落了?”
傅元影別開了臉,低聲道:“老爺子忘了麽?您當年答應過娘娘什麽了?”
“玉瑛?”瓊武川睜開了眼,壹臉茫然:“我……我答應她什麽了?”
人老了,最大的好處便是這個,眼看國丈又裝成了老糊塗,傅元影也不想多說了,瓊武川笑道:“雨楓啊,別老是生悶氣……其實穎超這件事,妳處置得很對。”傅元影低聲道:“老爺子是說……我把他交給了娘娘?”瓊武川呵呵笑道:“是啊,穎超這孩子心太高了……他不是寧不凡……卻老想當寧不凡,妳得想法子殺殺他的銳氣,不然他不能死心塌地守著芳兒。”
傅元影默默聽著,忽道:“老爺子,穎超是壹個劍客。”國丈笑道:“妳呢?妳不也是個劍客?”傅元影默然半晌,似想說些什麽,卻又忍住了,瓊武川察言觀色,呵呵笑道:“雨楓啊,妳就不怕穎超會落到妳這個下稍嗎?”
傅元影搖了搖頭,道:“老爺子多心了。我華山門下,壹人壹把劍。穎超的劍與我、與他師父的都不同,他遲早會找到自己的路子。”瓊武川笑道:“什麽路?死路?”
瓊武川有很多面貌,在江充面前,他像個瞎子,跌跌撞撞,讓人懶得計較。在景泰皇帝跟前,他又像個傻子,天天打擺子,到了華山門人眼中,他卻又似個神算子,樣樣事都算無遺策,總之千變萬化、莫衷壹是,根本就是壹個戲子。
傅元影並未頂嘴,眼見桌上還擱著壹碗湯藥,便端了過來,道:“老爺子,吃藥吧。”
瓊武川張開了嘴,如小孩般讓人餵了壹湯匙,道:“雨楓啊,妳也別總是掛記著不凡、掛記著穎超,今兒咱倆便來說說妳的事吧。”傅元影皺眉道:“我?我有什麽好說的?”國丈笑道:“妳曉得妳像誰嗎?”
傅元影無心回話,提起湯勺,正要再餵,卻聽瓊武川道:“妳像楊肅觀。”
傅元影微微壹楞,手上湯匙微微壹晃,險些濺了出來。瓊武川握住他的手,微微摩挲,道:“雨楓啊,妳可知我為何把妳比成楊肅觀?”傅元影搖了搖頭,示意不知,瓊武川呵呵笑道:“妳可曉得朝廷若是少了伍定遠,會怎麽地?”傅元影道:“兵兇戰危,勢若危卵。”
瓊武川狡黠壹笑:“那咱們現下有了伍定遠,就不兵兇戰危,勢若危卵了嗎?”
國丈所言不錯,伍定遠早已受了朝廷重用,可前線如火、京師被圍,仍舊是天下大亂,說來伍定遠便似壹帖臭郎中的老藥,延得了命,卻斷不了根。傅元影推測話意,沈吟道:“那照老爺子的意思,咱們這朝廷若是少了楊大人……”
“即刻便要……”瓊武川握住那塊鐵牌,咬牙道:“覆亡。”話到嘴邊,突又猛烈嗆咳,湯藥都嘔了出來,傅元影忙沿國丈的背心撫了撫,咳嗽立緩,便又取出布巾,替他擦拭嘴角。
瓊武川淡淡幾句話,卻也點出了傅元影的身價。華山有了寧不凡,能夠威震天下,有了呂應裳,可以添光增彩,可沒了傅元影,華山卻有立即傾倒之虞。
“懂了吧,雨楓。”瓊武川喘過了氣,便又嘶啞道:“妳……才是華山真正的大掌櫃啊。”
傅元影默默聽著,忽道:“老爺子過獎了,雨楓沒這個本事。”瓊武川笑道:“別介啊、雨楓,妳可知瓊某活到了八十歲,靠的是什麽嗎?”傅元影道:“老爺子靠的是神機妙算。”瓊武川戟指笑罵:“違心之論。要說神機妙算,我哪算得過劉敬?”傅元影道:“那老爺子靠的是什麽?”
瓊武川嘿嘿笑道:“我善觀人身上的‘氣’。”傅元影蹙眉道:“氣?您指的內力,還是……”
瓊武川傲然道:“氣!就是霸氣、英氣、秀氣、才氣,還有吾善養的浩然正氣。”傅元影點了點頭,瞧向床邊那塊“鎮國鐵衛之令”,頷首道:“這個正氣,老爺子養的真是太充足了。”
“他媽的!”瓊武川把手壹揮,弄翻了茶碗,罵道:“都到了今天,妳還是反對我投入客棧嗎?”傅元影欠身道:“雨楓不敢,老爺子向來神機妙算,做事自有道哩,何勞旁人過問?”
瓊武川惱道:“是,咱們都是龜孫子,最沒出息……可雨楓啊,妳到底有沒想過,似我這般膽小之人……那年復辟大戰,卻為何把身家性命都賭在楊肅觀身上?”
眼看國丈打翻了湯碗,弄得滿身是藥,又臟又黏,傅元影只得壹邊替他擦拭,壹邊道:“老爺子很看重楊大人的幹才,對嗎?”瓊武川斜目冷笑:“笑話。當年他不過是個小小兵部郎中,與我素無深交,我哪知他有何幹才?”
傅元影微微壹凜,也知國丈這話說到要緊處了,當年劉敬舉事之時,手握東廠,連結內外,來勢洶洶,瓊武川卻躲得不見蹤影。到了楊肅觀決心復辟時,不僅早被開革為民,尚且無兵無權,聲勢全不能與劉敬相比。卻不知瓊武川何以拒絕了劉敬,卻選擇與楊肅觀連手?
瓊武川喘了口氣,慢慢掙紮起身:“很奇怪吧……劉敬和我是多年交情,可他舉事之時,我卻嚇得噤若寒蟬,好似成了壹只縮頭烏龜,就怕擔上幹系……”傅元影找了壹件幹凈內衫,隨口道:“老爺子,風險是娘娘擔著。要是出了事,砍的是她的頭,傷不到您壹根寒毛。”
瓊武川大怒道:“妳說什麽?”把內衫搶了過來,拋到了地下,暴吼道:“混蛋東西!昨晚芳兒罵我的那些話,妳都聽到了?”傅元影道:“老爺子,您方才不還說我像楊大人?怎麽這會兒又是混蛋了?”
“混蛋……”瓊武川眼中現出壹絲惱怒,壹拳便望傅元影身上打去。砰地壹聲,“雨楓先生”肩頭略沈,便卸下了氣力,隨即撿起地下的內衫,替國丈換上。
國丈像個孩子,打過了人,氣也消解了幾分,又道:“雨楓,說正格的,妳和楊大人熟麽?”傅元影道:“當朝五輔,天絕傳人,我是久仰大名了。”
瓊武川道:“妳第壹回見到他時,想到了什麽?”傅元影道:“面帶城府,語無真心。”瓊武川輕蔑壹笑:“那妳只看到了皮相。”傅元影哦了壹聲:“那老爺子看到了什麽?”瓊武川道:“我見到了他身上的‘氣’。”傅元影笑了笑:“老爺子是驚嘆於楊大人身上的‘秀氣’,是嗎?”
“放妳媽的屁!”瓊武川脫下了衣服,說話更粗了,大聲道:“秀氣?什麽秀氣?我女色尚且不愛,還愛什麽男色?”傅元影微笑道:“那倒是。老爺子清心寡欲,天下罕見。”
“譏諷我是吧?”瓊武川火大了,正要再次出拳打人,卻聽傅元影道:“老爺子,手舉高。”拉住了國丈的手,帶他穿過了袖子,瓊武川咒罵幾聲,任他替自己穿衣,嘴中卻吼道:“聽好了!瓊某生於永樂年間,經五朝四帝,看盡天下風流人物,卻沒壹個人能像楊肅觀那樣……”頓了頓,話聲轉為低沈:“生具南面之氣。”
子曰:“雍也可使南面”,南面之氣,亦即王者之氣也,傅元影微起錯愕,隨即搖了搖頭,釋然壹笑:“老爺子,雨楓倒不知您還善於看相。”
瓊武川搖頭道:“雨楓,妳不是官場中人,自不信讖緯的道理。可咱們這些朝廷裏打滾的,最信者三,壹是命、壹是運、壹是氣!幾十年下來,潮起潮落,教妳不信也難。”
傅元影不置可否,含笑又道:“那照老爺子看來,楊大人的面相有何特異之處?”瓊武川深深嘆了口氣,道:“記得是景泰三十三年吧……那年楊肅觀打了個敗仗,到了奉天門前,那時我也剛好路過,猛壹見到他,突然被他嚇了壹大跳,險些滑了壹大跤……”
傅元影皺眉道:“滑了壹跤?怎會如此?”瓊武川喘息道:“這我也說不上來,我只記得那天他背對著奉天門,凝望北京,那壹刻,我突然覺得似曾相識,便在心裏直喊,對!這就是南面之相……我見過的……”
傅元影越聽越是不解,皺眉道:“老爺子的意思是……那時的楊大人看起來很面熟麽?”
瓊武川低聲道:“這我說不清楚……反正那壹幕就是似曾相識,好像在哪兒見過……自那之後,我便知道他絕非池中之物,早晚能飛騰人間……”
這話玄之又玄,傅元影自然聽不懂,他推測半晌,忽道:“是了,這是因為他長得像他父親楊遠,所以站在奉天門前,猛壹下便讓您誤認了,是嗎?”瓊武川搖頭道:“不是。楊遠身上沒有他那種氣。”傅元影道:“您的意思是說,他父子倆長得不像?”
瓊武川道:“說不像,那也不算,這楊家父子都是白面斯文,也算有幾分神似。可不知為何,他老子就沒那個氣,不似他這大兒子楊肅觀,讓我越看越覺得膽戰心驚……”
傅元影越聽越胡塗,便道:“老爺子,我這樣問吧,您初見楊大人時,他那時多大歲數?”瓊武川道:“那年他剛從少林寺還俗,年方十八。”傅元影道:“那時您便覺得他有‘王氣’麽?”
瓊武川搖頭嘆道:“那時……那時還不覺得。”傅元影微微壹笑:“這麽說來,這王者之氣還是與時俱進的?”瓊武川聽得諷刺,卻也不去反駁,只低聲喃喃:“看來……真是如此。”
老人家總是老眼昏花,疑神疑鬼,傅元影忍不住笑著搖頭了:“那劉總管、柳昂天呢?他倆見了楊肅觀,也覺得此人似曾相識嗎?”瓊武川搖頭道:“沒聽說過。”傅元影道:“那江充呢?聽說這江太師是真正懂得面相的,他也沒看出楊肅觀非比尋常?”
瓊武川木然道:“沒看出。所以他才成了我的……”突然嘿嘿壹笑,道:“手下敗將。”
景泰三雄之中,向以江充城府最深、劉敬智慧最高,柳昂天識人最廣,想這“江劉柳”三大權臣都瞧不出的事情,瓊武川卻能慧眼獨具,不能不讓傅元影半信半疑。眼看傅元影沒說話了,瓊武川低聲道:“雨楓,妳當我發瘋了,是嗎?”
傅元影搖頭道:“不,老爺子沒瘋,瘋的是我。”瓊武川惱道:“什麽意思?”傅元影淡淡地道:“老爺子是贏家。贏家是不會瘋的。”
確實如此,十年前復辟大決戰,江劉柳都死了,瓊武川卻活了下來,這是因為他站對了邊,靠對了人,從此躍居為朝廷第壹世家,無可動搖。不過傅元影卻不知道,原來當年國丈選擇了楊肅觀,竟是因為此人的面相。
“衛青不敗由天幸,李廣無功緣數奇”,人生許多事,往往莫名其妙,這就叫天命。傅元影也不想追問了,伸手拉住國丈的褲帶,將他的睡褲拉了下來。瓊武川道:“雨楓,妳別當我是老糊塗,告訴妳,我瓊武川為人做事,向來是有遠見的,好比說……好比說……”傅元影接口道:“出手打跑自己的孫女?”
“他媽的是!”瓊武川用力壹拳捶在床上,吼道:“存心氣我是吧?混蛋……妳說!說!我為啥要打芳兒?”國丈氣得結巴,傅元影卻是面不改色:“老爺子是怕那姓盧的,是麽?”
瓊武川喘道:“看妳跟了我這許多年,總算還不胡塗啊……”伸手搭住傅元影的肩頭,提腿進了褲腳,咬牙道:“妳……妳曉得那姓盧的像誰?”先前國丈才說楊肅觀身有王者之氣,現下又替那姓盧的看起相了,傅元影替他綁好了褲帶,便又取來外衣,道:“老爺子,手舉高。”
國丈微微喘氣,慢慢穿上了袖子,道:“那姓盧的,讓我……讓我想到了我兒子……”
傅元影聞言壹怔,停手下來,只見國丈撫面低喘:“雨楓,妳說……為何瓊翊樣樣都強過我,卻會比我早死?”傅元影無言以對,正要帶著國丈穿衣,卻聽壹聲哽咽:“因為他這個人……比誰都有良心……”話到嘴邊,突然激動起來:“所以他……註定要第壹個倒下!”
砰地壹聲,國丈把腳壹踢,猛聽轟然巨響,木桌飛了起來,撞破窗扉,直直墜到了樓下。屋外響起壹片驚喊:“怎麽了?”傅元影大聲道:“沒事!這兒有我!”
瓊武川雖然年老多病,可發起威來,氣力仍是駭人,看他須發淩亂,抄起了桌上鋼鞭,使勁壹掃,乓瑯壹聲,先將衣櫃掃得坍了,隨即反手壹抽,又將花瓶盡數砸破,傅元影也不勸阻,只退到了墻邊,靜靜看著老人家發泄。
良久良久,國丈放落了鋼鞭,雙肩不住抽動,竟似哭出了聲。傅元影替他穿上外衣,低聲道:“老爺子別這樣了。當年翊少爺他……是自願喝下那杯酒的。”驟然之間,老國丈仰起頭來,熱淚卻從眼角滑落,哽咽道:“雨楓,妳……妳也覺得我是個心狠手辣的父親麽?”
傅元影低聲道:“老爺子,這話該問您的壹雙兒女,不能問我。”嘆了口氣,便從衣架上提起朝袍,徑自披到瓊武川的肩上。
這件官袍色呈艷紅,雙肩繡以獅虎,正中補子則是壹只五彩火鳳,看瓊武川官袍加身,不知怎地,原本氣息短促,卻變得呼吸剛猛,原本須發淩亂,卻成了豪邁落拓,他不再是什麽糟老頭,而是本朝右柱國、復辟大戰第壹大特功,“奉天翊運推誠武臣”,瓊武川。
忙了半個時辰,國丈總算穿戴完畢,傅元影擦了擦汗,道:“老爺子,可以走了麽?”瓊武川左手叉腰,右手提著鋼鞭,靜靜地道:“妳坐下。”
人要衣裝、佛要金裝,天下最大的靈丹妙藥,就是這壹帖。瓊武川穿上了官袍,說話也威嚴了許多,眼看傅元影乖乖就範,便道:“我這兒有件大事,攸關我瓊家滿門生死,得立時與妳商量。”傅元影心下壹凜:“老爺子說的是怒蒼……”
國丈制住了說話:“錯了。什麽怒蒼之禍、八王之亂,都要不了妳我的性命,真正能見生死的事,是這壹件。”說話之間,便從枕頭下取出壹張字紙,塞到“雨楓先生”手裏。傅元影微微壹奇,正要開掌來看,瓊武川卻道:“先別忙。”
國丈目光深沈,傅元影卻是心下迷惑,看現今朝廷兩件大案,壹是立儲案,也就是是國丈嘴裏的“八王之亂”,再壹個便是“怒蒼之禍”,西郊阜城門外的那把怒火,前者包圍群臣、後者包圍京城,都是迫在眉睫的大事,可國丈卻似心有旁騖?
屋裏靜悄悄的,只見國丈握住傅元影的手,嗓音轉為柔和,低聲道:“雨楓,妳今年多大歲數了?”傅元影欠身道:“過了元宵,雨楓就五十了。”瓊武川伸手出來,輕撫他的面頰,低聲道:“這麽說來,那個秘密……妳也守了二十四年了?”不知不覺間,傅元影身上發起抖來了,寒聲道:“老爺子,妳…妳這話是……”國丈低聲道:“那杯毒酒又來了。”
砰地壹聲,傅元影竟爾滑倒在地,張嘴駭然,瓊武川輕聲道:“打開紙團。”傅元影大口喘息,勉強撐起身子,只見掌心裏有張字紙,已讓國丈揉成了壹團,他慢慢將之展開,卻見到了壹行字,見是:“天下第壹大笑話”。
傅元影顫聲道:“這……這是……”瓊武川道:“猜吧,天下第壹大笑話是什麽?”
傅元影臉色鐵青,慢慢將字條翻到背面,看到了壹行字跡,見是:“皇後娘娘的兒子……”
“不姓朱”。
“啊呀!”陡見這心裏埋藏二十年的秘密,饒那傅元影練了壹輩子的內功,還是忍不住雙手抱頭,狂叫出來,正要將紙條撕得稀爛,卻聽國丈道:“定下神來,什麽都別動。”
傅元影低頭喘息,咬牙切齒,又聽國丈附耳道:“把字條收好,咱們還得靠它指引,揪出幕後主使。”聽得提醒,傅元影啊了壹聲,這才想起這字條是個線索,他將字條貼肉藏好,深深吸了口氣,語音顫抖:“老爺子,這……這字條是打哪來的?”
瓊武川替他斟了杯熱茶,道:“喝下去,先定定神再說。”傅元影坐了下來,慢慢喝了幾口熱茶,讓心情定下,聽得國丈低聲道:“我壹早起床,見到案上壓了這張字條,拿起壹看,才知出了大事。”
傅元影咬牙切齒:“有內奸,我……我既刻召人來問。”正要轉身離房,卻又讓瓊武川拉住了:“不要節外生枝。這不是府裏人送進來的。”傅元影嘶啞道:“何……何以見得?”
瓊武川靜靜地道:“只要是我瓊家的人,哪怕是壹條狗、壹只雞,都會受這字條牽連。誰會傻到拿自己全家的性命玩笑?”
姜是老的辣,這張字條若是泄漏出去,那便是罪夷九族的大罪。瓊府上下兩百余口人,無壹人能脫身。國丈不愧經歷過兩次復辟政變,生死關頭,拿捏精準。反倒是傅元影方寸大亂,喘了口氣,低聲又問:“那……那照老爺子看,這字條是什麽人送進來的?”
瓊武川道:“我推算過,此事只有兩個可能。其壹,便是立儲案。”傅元影心下壹醒,忙道:“徽唐徐豐魯?”瓊武川道:“正是。現今立儲在即,這些籓王兔崽子早在抓我瓊家的把柄,掘地三尺,無所不用其極,這便讓他們查出了蛛絲馬跡。那也未可知。”
傅元影聽著聽,忽道:“不會。”這回輪瓊武川“哦”了壹聲:“何以見得?”傅元影道:“老爺子,世上的秘密只消經過我的手,便不會再外泄。”傅元影這話說得斬釘截鐵,斷斷無轉圜余地了,料來“徽唐徐豐魯”便把瓊家的祖墳都掘開了,也挖不出這字條上的秘密,此間事情,必是他人所為。
“喀……嗨……”瓊武川推開窗扉,朝外吐了壹口膿痰。傅元影又道:“老爺子方才說了兩個可能,另壹個是什麽?”瓊武川提起茶碗,漱了漱口,道:“義勇人。”
“義……義勇人?”傅元影面色微變,瓊武川皺眉道:“怎麽?妳也聽過他們?”傅元影低聲道:“我……我曾聽若林提過幾次,說朝廷裏有壹幫人專和楊大人作對,好似叫‘反楊十大臣’,也不知是真是假。”瓊武川嘿嘿壹笑:“好妳個呂若林,明察秋毫啊……”
傅元影不願拉師兄下水,便轉過了話頭,道:“老爺子,您和這‘義勇人’有仇麽?”瓊武川道:“我是楊肅觀的盟友,這義勇人卻是楊大人的死敵,妳說咱們倆家有仇沒仇?”
傅元影低聲道:“這些人到底是什麽來歷?何以這般憎恨楊大人?”瓊武川道:“這些人有的是朝中大臣,有的是江湖術士,全都吃過楊肅觀的虧,於是便以柳昂天的名頭為號召,結盟立誓。”傅元影納悶道:“柳昂天?這人不是過世了?為何要以他為號召?”瓊武川道:“相傳柳昂天……死於楊肅觀之手……”傅元影心下壹凜,立時默然低頭,不再多問了。
守密之難,難如登天,想傅元影的肚子早被秘密裝得滿了,如何還裝得下新東西?聽得秘密又來了,忙掉過話頭,低聲道:“老爺子,倘使這字條真是義勇人搞的鬼……那他們是要……”
瓊武川附耳道:“他們是要我背叛‘鎮國鐵衛’,下手扳倒楊大人。”
傅元影心頭大震:“那……那要是老爺子不從呢?”瓊武川道:“這張字條便會放到萬歲爺的案上,妳想咱們瓊家會如何?”這話如同雷霆閃電,直打得“雨楓先生”作聲不得。良久良久,聽他低聲道:“老爺子,妳想過向楊大人求援嗎?”
瓊武川道:“這事若讓楊大人知道,我瓊家立時便倒。”傅元影聞言壹楞:“老爺子,妳……妳不也是鎮國鐵衛的……”瓊武川嘿嘿壹笑:“雨楓,妳還是沒弄懂啊,妳可知義勇人的靠山是什麽人?”傅元影沈吟道:“是……是宰輔何大人?還是……伍大都督?”
瓊武川搖頭道:“錯了,是皇上。”傅元影霍地起身,顫聲道:“皇上?”瓊武川淡淡地道:“妳可知皇上怎麽稱呼楊肅觀?”他笑了笑,自知傅元影猜不出,便道:“楊黨。”
眼看傅元影呼吸加促,瓊武川便嘆了口氣,道:“當年復辟政變之後,皇上立時察覺朝廷藏了所謂的‘楊黨’,遍布朝野。妳且想想,皇上好容易才拿回了大權,卻又聽說朝廷裏另有黨派集結,他會怎麽想?”傅元影低聲道:“日夜憂懼。”瓊武川木然道:“妳說對了。”
史記韓信傳有言:“狡兔死、走狗烹;飛鳥盡、良弓藏”,臥榻之旁,豈容有人鼾睡?依此觀之,楊肅觀其實形勢危殆,絕非外人想象得那般大權在握。
傅元影低聲道:“老爺子……皇上為何會隱忍楊大人至今?”國丈道:“怒蒼山。”
傅元影啊了壹聲,卻也聽懂了。正所謂飛鳥不盡、良弓不藏,只要秦仲海未倒,皇上便不會和楊肅觀撕破臉。傅元影點了點頭,低聲道:“難怪老爺子會說‘義勇人’的靠山便是皇上。原來藏著這壹層道理。”
瓊武川道:“沒錯,皇上不能沒有楊肅觀,卻又信不過楊肅觀,為了壓制楊黨的勢力,皇上對反楊大臣總是恩寵有佳,若非如此,那年馬人傑把皇上罵得壹文不值,如何能留下壹條命?”
“馬人傑?”傅元影皺眉道:“他……他也是反楊大臣?”國丈道:“客棧裏有句話,叫做‘俊傑萬山風’。妳猜猜,這個‘傑’字指的是誰?”傅元影低聲道:“便是馬人傑?”
國丈道:“就是他。反楊十大臣,善穆義勇人,這‘俊傑萬山風’裏的‘風’字,正是柳昂天的兒子柳雲風,‘萬’字則是現任都察院的大頭兒萬吉祥。上頭那個‘俊’字,則是內閣輔臣牟俊逸,妳別看馬人傑官大,論資排輩,還只能排到了第七。”
聽得朝廷重臣雲集,專以反楊為己任,傅元影自也暗暗心驚,忙道:“除了這五人,另外還有誰?”國丈道:“頭牌五位,至今尚未現身。客棧雖說到處刺探,至今也還是沒個定論。”傅元影低聲道:“這些人從不露面,彼此怎麽聯系?”
國丈道:“這就不清楚了。每回朝堂上要與楊黨爭執,多由牟俊逸、馬人傑他們發動,不過除開‘反楊’這門功課,這些大臣平日多半自行其是,就拿這餓鬼東渡的事來說,牟俊逸主戰、馬人傑主和,兩人便各執壹詞,公開對著幹了。”
傅元影對朝政不甚關心,心裏只掛記著字條,又道:“那照老爺子看來,義勇人的大首領究竟是什麽人?”國丈嘆了口氣,道:“此人神出鬼沒,仿佛有百變之身。我幾次差人跟蹤馬人傑,他卻都能及時脫身,至今仍是壹無所獲。”
傅元影微微壹凜:“老爺子派人跟蹤過馬大人?我怎麽不知情?”國丈淡淡地道:“妳們華山玉清是名門正派,有些事情不好出面。我便沒通知妳。”
傅元影咳嗽壹聲。自知國丈私下還養了壹批探子。白日裏的事情,多由華山門下代勞,夜裏的事情,則交由這批密探來幹。雖說武功比不上華山的大劍客們,下手卻狠辣了許多。
傅元影默默聽著,忽道:“老爺子,皇上知道您也是‘楊黨’嗎?”瓊武川嘿嘿壹笑:“妳說呢?皇上知不知道?”傅元影心下壹凜,忙道:“皇上……皇上已經知道了?”
瓊武川裂嘴壹笑:“知道?豈止是知道?那年楊肅觀挨了壹槍,從永定河裏爬了出來,妳曉得他第壹個找的是誰?就是我瓊武川!妳可知那時他渾身浴血、命在旦夕,卻拉著我去見了誰?見的就是皇上!那時瓊某賭上了身家性命,與楊肅觀歃血為盟,又是誰拉著咱倆的手,感激涕零、自稱永世不忘今日之恩?告訴妳,那個人便是咱們今日的……”提起鋼鞭壹砸,厲聲道:“皇上!”
楊黨、楊黨,昨日之舊愛,轉眼成今日之大患,傅元影默然半晌,低聲道:“老爺子這場富貴,來得著實不易。”國丈仰起頭來,怔怔嘆了口氣:“來得實在是……太難太難了……”
屋裏靜了下來,傅元影與瓊武川對望壹眼,兩人各自想著自己的心事,誰也沒作聲。
良久良久,聽得傅元影道:“老爺子,皇上想過要拔掉妳麽?”瓊武川道:“那還不至於。我手裏有張保命符,只消這張符還靈驗,我就不會有事。”傅元影道:“您說得是娘娘。”
瓊武川道:“沒錯,就是玉瑛。楊肅觀是有遠見的人,當年他拉攏我,其實為的就是這條裙帶。只消玉瑛還在,他與皇上之間便有個緩頰,可掉句話來說,要是這條裙帶汙了臟了……”聲音漸漸低緩,嘆道:“妳想他會怎麽做?”傅元影道:“他會壯士斷腕。”
瓊武川木然道:“妳說對了。依我推算,楊肅觀壹旦得知消息,非但不會替我等遮掩,反會率先揭發此事,否則他若受我瓊家所累,怕也要跟著壹齊倒了。”
前有狼、後有虎,這兒是九五至尊,正統皇帝,那兒卻是復辟奸雄,“鎮國鐵衛”的大掌櫃,無論向哪方開戰,都是死路壹條。如今腹背受敵,國丈卻連客棧的密探也不能用了,說來“紫雲軒”上下別無依靠,只能看華山高手的作為。
華山門人不少,堪用的大材卻不多,先看蘇穎超渾渾噩噩,再看瓊芳少女驕狂,耍耍威風可以,謀劃大事則遠遠不行,推來算去,只剩下大師兄呂應裳可以援手。只是這“若林先生”總是聰明得過了頭,壹旦察覺大事不妙,只怕腳底抹油,又要跑得不見蹤影了。
傅元影嘆了口氣,緩緩提起自己的佩劍,道:“老爺子希望我怎麽做?”
瓊武川道:“倘這字條是八王所為,咱們便有著力之處。畢竟‘徽唐徐豐魯’所求只在東宮,不會把咱們望死路上送,可若是義勇人所為,事情便難善了。”
傅元影垂首無語,國丈也是撫面沈思,良久良久,聽得老人家低聲道:“芳兒還在楊家,對嗎?”傅元影道:“是。”瓊武川道:“那好。妳這兩日先別急著接她回來,先把她留在楊府,若真出事了,也好扯楊肅觀下水。至於義勇人那邊……”喘氣半晌,道:“妳替我去找馬人傑,探探他的口風。”
傅元影忙道:“老爺子,馬大人是兵部尚書,咱們若是用強……”瓊武川道:“沒人要妳用強。馬人傑雖是義勇人,卻也是個明白人,當今怒蒼兵臨城下,大禍在前,他絕不會坐視咱們瓊家在此刻垮臺。”傅元影忙道:“萬壹……萬壹馬大人不願幫這個忙,那咱們……”
瓊武川道:“那也沒什麽,真到了絕路上,瓊某便打開西郊阜城門,恭迎怒王進京。”
轟地壹聲,傅元影腦中壹片空白,耳中更是嗡嗡作響,竟連話也說不出來了。
餓鬼圍城,人心惶惶,看國丈雖是皇帝親家,卻也生出了反心,何況其它?眼看傅元影臉色鐵青,瓊武川便又道:“雨楓,兵兇戰危,沒人是忠臣,也沒人是奸臣,大家都只求個滿門保全、全身而退。他們若逼急了我,姓瓊的只有反。”
對面是楊肅觀,背後是義勇人,頭上還有個正統皇帝,三方包夾,國丈的出路無他,恐怕真是在阜城門了,傅元影怔怔望著窗外,又聽國丈道:“好了,事不宜遲,妳趕緊吩咐家人收拾收拾,說咱們今夜要在紅螺寺裏掛單,絕不能讓皇上起了疑心。”
傅元影低聲答應了,正要轉身離開,卻聽國丈道:“且慢,我還有件事問妳。”傅元影躬身道:“老爺子請吩咐。”國丈撐起了身子,慢慢來到傅元影身邊,搭住了他的肩頭,壓低嗓子,嘶啞地道:“雨楓,那個孩子……”傅元影極深極深的吸了口氣,聽得瓊武川附耳道:“妳到底藏在什麽地方?”
傅元影低頭沈默,並未言語。國丈皺眉道:“都二十多年了,妳還信不過我?”
傅元影道:“老爺子,我答應過翊少爺了。這事不能說。”瓊武川搖頭嘆氣:“妳想得太多了,虎毒不噬子,我還能害了自己的外孫麽?我只想問問妳,那孩子平安麽?”
傅元影道:“老爺子放心,這二十多年來,雨楓壹直照看著他。”瓊武川雙眉壹軒,道:“壹直?”傅元影看似目光望地,實則雙眼圓睜,眉毛更吊了起來,國丈察言觀色,立時猛烈咳嗽,喘道:“那就好……那就好……有妳照看著……那我也放心了……”
傅元影躬身行禮,便又走下樓去,木板嘎滋嘎滋地響了起來,漸漸遠去。國丈把耳朵貼在墻上,傾聽良久,確信傅元影走遠了,方才道:“招度羅。”
喊聲壹出,屋梁上忽然垂下壹條繩索,降臨了壹道黑影,行到國丈面前,躬身道:“三當家。”瓊武川道:“方才我和傅雨楓的對答,妳都聽到了?”那黑影道:“聽到了。”瓊武川道:“很好,我現下有個差事給妳,知道是什麽嗎?”
黑影道:“三當家要找那個孩子。”瓊武川木然道:“妳說對了。那孩子理應躲在華山門下,算來已有二十四歲,姓啥名誰不知道、樣貌如何也不清楚,但有件事錯不了……”
黑影道:“資質,是嗎?”瓊武川道:“沒錯。蘇穎超成不了大器,華山絕學卻不能失傳。我要妳順著‘三達劍譜’去找,看看傅元影把‘三達劍’交給了誰,懂得這個意思嗎?”
那黑影道:“小人懂得。等找到那孩子以後,國丈是要……”瓊武川深深吸了口氣:“這我自有處置。”那黑影默然半晌,並不做聲,瓊武川惱道:“怎麽?信不過我?”
黑影道:“小人不敢。”他拉住了繩索,正要回到梁上,忽又頓了頓,道:“三當家,您方才說要迎怒蒼入京,該是玩笑話吧?”瓊武川道:“那是說給下面人聽的。妳要不放心,不妨把這話轉給大掌櫃。”那黑影道:“小人不敢。”
瓊武川道:“去吧,記得告訴大掌櫃,瓊某人的麻煩,瓊某自個兒收拾,絕不讓他操心。”
黑影拱手致意,身子慢慢飄了起來,順延繩索,回到了梁上。瓊武川立時爬起身來,動作迅捷之至,壹時貼耳在墻,確信黑影離去了,方才罵道:“壹群混蛋!”
木階嘎嘎作響,瓊武川推開了窗扉,朝窗外吐了口痰,便也拾級而下,離開了精舍。
幾十年來,國丈住的地方都沒變,壹直在紫雲軒的“碧濤樓”,此地壹來鄰近竹林,綠影碧濤,最能陶冶性情,二來地勢高,不但可瞧見瓊府的家廟議事廳,還能望見少閣主的臥房,紫雲軒的過去、未來,乃至於當下,無不在掌握之中。
天色嚴寒,慢慢又飄起了雪,也不知過了多久,園林裏奔來了壹人,喊道:“傅師叔!傅師叔!您在這兒嗎?”來人年紀頗輕,腰上帶劍,正是華山弟子施得興,來到了精舍下,不由愕然道:“師叔,您……您怎麽坐在這兒?”
園林裏盤膝正坐壹人,正是傅元影,看他滿頭霜雪寒花,不知在這兒待了多久。
碧濤樓可見過去、可見未來,卻見不到腳下。傅元影未曾躲藏,他只是靜靜坐著,國丈與招度羅來來去去,都沒發覺他,因為他是寧不凡的師弟,華山那套藏氣功夫,他也練了四十年。
傅元影盤膝而坐,將長劍平放腿上,不發壹語,施得興低聲道:“師叔,您……您還好麽?”
傅元影撫挲劍身,默然良久,方才道:“找我有事?”施得興見他神氣古怪,心裏有些害怕,低聲道:“外頭……外頭來了個太監,說晚間八世子要比武了,要咱們趕緊挑個大伴習出來,他好把名單送進宮裏。”傅元影皺眉道:“什麽大伴習?這是什麽名堂?”
施得興低聲道:“這……這弟子也不大清楚,好像是陪世子練武的伴當,那太監說……說這人選挺要緊的。趙五師祖找不到呂師伯,便要弟子來精舍找您,說要商量這個人選。”
傅元影緩緩站起身來,忽道:“陳得福呢?見到他了麽?”施得興嘆道:“那小子不知又發了什麽瘋,壹早便哭哭啼啼,躲在後廚不出來,說自己闖了大禍……”
傅元影點了點頭,握住了劍柄,“嗡”地壹聲大響,劍身已然出鞘,那弟子嚇了壹跳:“師叔,您……您怎麽了?”
“沒什麽……”當地壹聲,傅元影伸指在劍刃上壹彈,長劍前後擺蕩,發出了嗡嗡低響,聽他道:“只是看這柄劍藏了這麽多年……”說著從懷裏取出幹布,在劍上擦了擦,淡淡地道:“也該是擦亮它的時候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