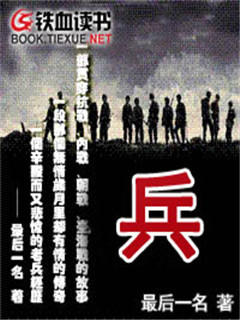- [ 免費 ] 前言
- [ 免費 ] 第壹章 槍王(壹)
- [ 免費 ] 第壹章 槍王(二)
- [ 免費 ] 第壹章 槍王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章 壯丁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章 壯丁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章 壯丁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章 軍歌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章 軍歌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章 軍歌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章 空襲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章 空襲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章 空襲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章 狙擊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章 狙擊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章 狙擊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章 敵後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章 敵後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章 敵後(三)
- [ 免費 ] 第七章 兄弟(壹)
- [ 免費 ] 第七章 兄弟(二)
- [ 免費 ] 第七章 兄弟(三)
- [ 免費 ] 第八章 清鄉(壹)
- [ 免費 ] 第八章 清鄉(二)
- [ 免費 ] 第八章 清鄉(三)
- [ 免費 ] 第九章 回歸(壹)
- [ 免費 ] 第九章 回歸(二)
- [ 免費 ] 第九章 回歸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章 石牌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章 石牌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章 石牌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 昆明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 昆明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 昆明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 空戰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 空戰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 空戰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 車行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 車行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 車行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 逼婚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 逼婚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 逼婚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 營副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 營副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 營副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 喝酒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 喝酒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 喝酒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 軍令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 軍令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 軍令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 急救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 急救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 急救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 懲奸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 懲奸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 懲奸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 雙殺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 雙殺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 雙殺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壹章 蔣幹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壹章 蔣幹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壹章 蔣幹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二章 副官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二章 副官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二章 副官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三章 疑兵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三章 疑兵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三章 疑兵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四章 激戰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四章 激戰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四章 激戰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五章 誓師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五章 誓師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五章 誓師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六章 孤軍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六章 孤軍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六章 孤軍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七章 拼刺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七章 拼刺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七章 拼刺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八章 苦戰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八章 苦戰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八章 苦戰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九章 追令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九章 追令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九章 追令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十章 慘勝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十章 慘勝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十章 慘勝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壹章 賞罰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壹章 賞罰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壹章 賞罰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二章 收容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二章 收容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二章 收容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三章 奪兵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三章 奪兵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三章 奪兵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四章 常德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四章 常德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四章 常德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五章 諜影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五章 諜影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五章 諜影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六章 虎賁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六章 虎賁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六章 虎賁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七章 危城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七章 危城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七章 危城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八章 外圍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八章 外圍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八章 外圍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九章 城廂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九章 城廂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九章 城廂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十章 鏖戰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十章 鏖戰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十章 鏖戰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壹章 網開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壹章 網開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壹章 網開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二章 破門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二章 破門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二章 破門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三章 巷戰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三章 巷戰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三章 巷戰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四章 無衣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四章 無衣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四章 無衣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五章 白馬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五章 白馬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五章 白馬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六章 復城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六章 復城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六章 復城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六章 復城(四)
- [ 免費 ] 第四七章 淒絕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七章 淒絕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七章 淒絕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八章 悲憤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八章 悲憤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八章 悲憤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八章 悲憤(四)
- [ 免費 ] 第四九章 陸大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九章 陸大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九章 陸大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十章 會審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十章 會審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十章 會審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十章 會審(四)
- [ 免費 ] 第五壹章 君側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壹章 君側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壹章 君側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二章 重慶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二章 重慶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二章 重慶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三章 敗潰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三章 敗潰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三章 敗潰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四章 芷江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四章 芷江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四章 芷江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五章 湘西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五章 湘西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五章 湘西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五章 湘西(四)
- [ 免費 ] 第五六章 野戰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六章 野戰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六章 野戰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六章 野戰(四)
- [ 免費 ] 第五七章 雪峰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七章 雪峰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七章 雪峰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七章 雪峰(四)
- [ 免費 ] 第五八章 反擊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八章 反擊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八章 反擊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九章 洞口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九章 洞口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九章 洞口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九章 洞口(四)
- [ 免費 ] 第六十章 奪藥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十章 奪藥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十章 奪藥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十章 奪藥(四)
- [ 免費 ] 第六壹章 精銻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壹章 精銻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壹章 精銻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壹章 精銻(四)
- [ 免費 ] 第六二章 包夾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二章 包夾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二章 包夾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二章 包夾(四)
- [ 免費 ] 第六三章 轉機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三章 轉機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三章 轉機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三章 轉機(四)
- [ 免費 ] 第六四章 山門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四章 山門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四章 山門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四章 山門(四)
- [ 免費 ] 第六五章 圍堵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五章 圍堵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五章 圍堵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五章 圍堵(四)
- [ 免費 ] 第六六章 無言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六章 無言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六章 無言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六章 無言(四)
- [ 免費 ] 第六七章 勝利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七章 勝利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七章 勝利(三)
- [ 免費 ] 第壹章 和談(壹)
- [ 免費 ] 第壹章 和談(二)
- [ 免費 ] 第壹章 和談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章 停戰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章 停戰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章 停戰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章 團聚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章 團聚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章 團聚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章 還鄉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章 還鄉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章 還鄉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章 整編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章 整編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章 整編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章 策反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章 策反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章 策反(三)
- [ 免費 ] 第七章 情誼(壹)
- [ 免費 ] 第七章 情誼(二)
- [ 免費 ] 第七章 情誼(三)
- [ 免費 ] 第八章 嫁禍(壹)
- [ 免費 ] 第八章 嫁禍(二)
- [ 免費 ] 第八章 嫁禍(三)
- [ 免費 ] 第九章 武漢(壹)
- [ 免費 ] 第九章 武漢(二)
- [ 免費 ] 第九章 武漢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章 宴請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章 宴請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章 宴請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 集結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 集結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 集結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 聲東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 聲東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 聲東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 交手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 交手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 交手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 反間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 反間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 反間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 兩難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 兩難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 兩難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 相煎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 相煎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 相煎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 袍澤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 袍澤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 袍澤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 突圍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 突圍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 突圍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 灰心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 灰心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 灰心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 營救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 營救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 營救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壹章 行刑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壹章 行刑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壹章 行刑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二章 續命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二章 續命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二章 續命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三章 轉戰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三章 轉戰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三章 轉戰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四章 龍鳳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四章 龍鳳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四章 龍鳳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五章 口袋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五章 口袋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五章 口袋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六章 交鋒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六章 交鋒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六章 交鋒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七章 圍突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七章 圍突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七章 圍突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八章 榮辱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八章 榮辱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八章 榮辱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九章 群毆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九章 群毆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九章 群毆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十章 抵角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十章 抵角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十章 抵角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壹章 解圍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壹章 解圍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壹章 解圍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二章 分道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二章 分道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二章 分道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三章 蘇北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三章 蘇北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三章 蘇北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四章 宿遷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四章 宿遷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四章 宿遷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五章 攻守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五章 攻守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五章 攻守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六章 故人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六章 故人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六章 故人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七章 雷霆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七章 雷霆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七章 雷霆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八章 山東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八章 山東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八章 山東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九章 夜襲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九章 夜襲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九章 夜襲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十章 沂蒙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十章 沂蒙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十章 沂蒙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壹章 救援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壹章 救援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壹章 救援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二章 蒙陰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二章 蒙陰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二章 蒙陰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三章 十勝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三章 十勝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三章 十勝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四章 偷襲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四章 偷襲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四章 偷襲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五章 坦埠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五章 坦埠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五章 坦埠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六章 歸去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六章 歸去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六章 歸去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七章 分兵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七章 分兵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七章 分兵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八章 南麻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八章 南麻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八章 南麻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九章 接火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九章 接火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九章 接火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十章 地堡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十章 地堡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十章 地堡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壹章 膠著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壹章 膠著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壹章 膠著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二章 探聽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二章 探聽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二章 探聽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三章 沂河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三章 沂河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三章 沂河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四章 崮山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四章 崮山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四章 崮山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五章 反水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五章 反水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五章 反水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六章 歷山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六章 歷山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六章 歷山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七章 無義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七章 無義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七章 無義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八章 轉攻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八章 轉攻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八章 轉攻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九章 還槍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九章 還槍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九章 還槍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十章 坦克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十章 坦克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十章 坦克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壹章 遭遇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壹章 遭遇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壹章 遭遇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二章 圍缺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二章 圍缺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二章 圍缺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三章 逆襲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三章 逆襲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三章 逆襲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四章 進擊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四章 進擊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四章 進擊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五章 追伏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五章 追伏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五章 追伏(三)
- [ 免費 ] 第壹章 永城(壹)
- [ 免費 ] 第壹章 永城(二)
- [ 免費 ] 第壹章 永城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章 信陽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章 信陽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章 信陽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章 避實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章 避實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章 避實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章 就虛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章 就虛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章 就虛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章 天險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章 天險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章 天險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章 夜仗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章 夜仗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章 夜仗(三)
- [ 免費 ] 第七章 轉出(壹)
- [ 免費 ] 第七章 轉出(二)
- [ 免費 ] 第七章 轉出(三)
- [ 免費 ] 第八章 布網(壹)
- [ 免費 ] 第八章 布網(二)
- [ 免費 ] 第八章 布網(三)
- [ 免費 ] 第九章 柳林(壹)
- [ 免費 ] 第九章 柳林(二)
- [ 免費 ] 第九章 柳林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章 包圍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章 包圍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章 包圍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 脫險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 脫險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 脫險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 探親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 探親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 探親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 整軍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 整軍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 整軍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 襲擾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 襲擾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 襲擾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 包信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 包信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 包信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 並行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 並行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 並行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 洛陽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 洛陽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 洛陽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 測字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 測字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 測字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 互搏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 互搏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 互搏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 戰書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 戰書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 戰書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壹章 較量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壹章 較量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壹章 較量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二章 孤註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二章 孤註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二章 孤註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三章 鬥槍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三章 鬥槍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三章 鬥槍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四章 尹劍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四章 尹劍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四章 尹劍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五章 杯酒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五章 杯酒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五章 杯酒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六章 驛城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六章 驛城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六章 驛城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七章 上蔡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七章 上蔡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七章 上蔡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八章 圍城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八章 圍城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八章 圍城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九章 回槍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九章 回槍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九章 回槍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十章 絞殺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十章 絞殺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十章 絞殺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壹章 奪橋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壹章 奪橋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壹章 奪橋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二章 土木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二章 土木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二章 土木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三章 退兵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三章 退兵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三章 退兵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四章 汝南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四章 汝南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四章 汝南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五章 睢杞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五章 睢杞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五章 睢杞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六章 急進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六章 急進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六章 急進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七章 淮陽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七章 淮陽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七章 淮陽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八章 空城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八章 空城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八章 空城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九章 無功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九章 無功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九章 無功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十章 兵團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十章 兵團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十章 兵團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壹章 黃維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壹章 黃維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壹章 黃維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二章 遊行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二章 遊行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二章 遊行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三章 將帥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三章 將帥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三章 將帥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四章 東調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四章 東調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四章 東調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五章 夏陽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五章 夏陽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五章 夏陽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六章 爭先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六章 爭先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六章 爭先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七章 阜陽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七章 阜陽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七章 阜陽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八章 潁河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八章 潁河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八章 潁河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九章 北進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九章 北進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九章 北進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十章 渦河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十章 渦河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十章 渦河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壹章 蒙城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壹章 蒙城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壹章 蒙城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二章 黃莊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二章 黃莊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二章 黃莊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三章 四團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三章 四團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三章 四團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四章 爭奪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四章 爭奪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四章 爭奪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五章 烈焰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五章 烈焰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五章 烈焰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六章 蕭蕭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六章 蕭蕭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六章 蕭蕭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七章 板橋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七章 板橋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七章 板橋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八章 澮河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八章 澮河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八章 澮河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九章 南坪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九章 南坪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九章 南坪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十章 趙括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十章 趙括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十章 趙括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壹章 坐失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壹章 坐失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壹章 坐失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二章 內鬼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二章 內鬼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二章 內鬼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三章 守死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三章 守死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三章 守死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四章 火焰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四章 火焰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四章 火焰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五章 雙堆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五章 雙堆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五章 雙堆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六章 飛將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六章 飛將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六章 飛將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七章 南京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七章 南京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七章 南京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八章 棄生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八章 棄生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八章 棄生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九章 赴死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九章 赴死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九章 赴死(三)
- [ 免費 ] 第七十章 楚歌(壹)
- [ 免費 ] 第七十章 楚歌(二)
- [ 免費 ] 第七十章 楚歌(三)
- [ 免費 ] 第七壹章 王莊(壹)
- [ 免費 ] 第七壹章 王莊(二)
- [ 免費 ] 第七壹章 王莊(三)
- [ 免費 ] 第七二章 浴血(壹)
- [ 免費 ] 第七二章 浴血(二)
- [ 免費 ] 第七二章 浴血(三)
- [ 免費 ] 第七三章 四散(壹)
- [ 免費 ] 第七三章 四散(二)
- [ 免費 ] 第七三章 四散(三)
- [ 免費 ] 第七四章 沖殺(壹)
- [ 免費 ] 第七四章 沖殺(二)
- [ 免費 ] 第七四章 沖殺(三)
- [ 免費 ] 第七五章 奈何(壹)
- [ 免費 ] 第七五章 奈何(二)
- [ 免費 ] 第七五章 奈何(三)
- [ 免費 ] 第壹章 夜奔(壹)
- [ 免費 ] 第壹章 夜奔(二)
- [ 免費 ] 第壹章 夜奔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章 浴火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章 浴火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章 浴火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章 重生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章 重生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章 重生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章 尋夫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章 尋夫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章 尋夫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章 未死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章 未死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章 未死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章 觀音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章 觀音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章 觀音(三)
- [ 免費 ] 第七章 開顱(壹)
- [ 免費 ] 第七章 開顱(二)
- [ 免費 ] 第七章 開顱(三)
- [ 免費 ] 第八章 破相(壹)
- [ 免費 ] 第八章 破相(二)
- [ 免費 ] 第八章 破相(三)
- [ 免費 ] 第九章 半面(壹)
- [ 免費 ] 第九章 半面(二)
- [ 免費 ] 第九章 半面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章 訴苦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章 訴苦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章 訴苦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 靈犀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 靈犀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 靈犀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 故舊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 故舊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 故舊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 軍制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 軍制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 軍制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 刺客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 刺客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 刺客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 渡江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 渡江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 渡江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 疾馳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 疾馳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 疾馳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 報警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 報警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 報警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 西向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 西向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 西向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 父子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 父子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 父子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 娜娜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 娜娜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 娜娜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壹章 小差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壹章 小差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壹章 小差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二章 故地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二章 故地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二章 故地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三章 困局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三章 困局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三章 困局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四章 諜碼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四章 諜碼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四章 諜碼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五章 進山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五章 進山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五章 進山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六章 寶藏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六章 寶藏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六章 寶藏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七章 山寺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七章 山寺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七章 山寺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八章 迷魂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八章 迷魂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八章 迷魂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九章 火並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九章 火並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九章 火並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十章 老徐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十章 老徐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十章 老徐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壹章 殘兵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壹章 殘兵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壹章 殘兵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二章 人質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二章 人質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二章 人質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三章 佛面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三章 佛面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三章 佛面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四章 彭家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四章 彭家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四章 彭家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五章 蛇心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五章 蛇心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五章 蛇心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六章 峰回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六章 峰回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六章 峰回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七章 真相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七章 真相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七章 真相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八章 曾識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八章 曾識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八章 曾識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九章 辰州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九章 辰州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九章 辰州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十章 招安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十章 招安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十章 招安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壹章 烏合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壹章 烏合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壹章 烏合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二章 打獵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二章 打獵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二章 打獵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三章 夜宴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三章 夜宴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三章 夜宴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四章 韓奇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四章 韓奇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四章 韓奇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五章 轉變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五章 轉變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五章 轉變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六章 歸塵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六章 歸塵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六章 歸塵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七章 急援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七章 急援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七章 急援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八章 奇襲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八章 奇襲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八章 奇襲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九章 追逃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九章 追逃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九章 追逃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十章 高偉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十章 高偉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十章 高偉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壹章 元江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壹章 元江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壹章 元江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二章 無量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二章 無量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二章 無量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三章 虛張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三章 虛張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三章 虛張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四章 單刀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四章 單刀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四章 單刀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五章 赴會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五章 赴會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五章 赴會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六章 投誠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六章 投誠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六章 投誠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七章 過年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七章 過年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七章 過年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八章 同樂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八章 同樂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八章 同樂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九章 希望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九章 希望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九章 希望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十章 起舞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十章 起舞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十章 起舞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壹章 風聲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壹章 風聲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壹章 風聲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二章 日記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二章 日記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二章 日記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三章 審查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三章 審查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三章 審查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四章 人證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四章 人證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四章 人證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五章 舊案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五章 舊案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五章 舊案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六章 陽謀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六章 陽謀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六章 陽謀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七章 迢遙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七章 迢遙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七章 迢遙(三)
- [ 免費 ] 第壹章 遼東(壹)
- [ 免費 ] 第壹章 遼東(二)
- [ 免費 ] 第壹章 遼東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章 入朝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章 入朝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章 入朝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章 首戰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章 首戰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章 首戰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章 雲山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章 雲山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章 雲山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章 阻戰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章 阻戰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章 阻戰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章 疲兵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章 疲兵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章 疲兵(三)
- [ 免費 ] 第七章 烈火(壹)
- [ 免費 ] 第七章 烈火(二)
- [ 免費 ] 第七章 烈火(三)
- [ 免費 ] 第八章 熊熊(壹)
- [ 免費 ] 第八章 熊熊(二)
- [ 免費 ] 第八章 熊熊(三)
- [ 免費 ] 第九章 總結(壹)
- [ 免費 ] 第九章 總結(二)
- [ 免費 ] 第九章 總結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章 押解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章 押解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章 押解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 俘虜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 俘虜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 俘虜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 夜行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 夜行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 夜行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 狼嚎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 狼嚎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 狼嚎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 安東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 安東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 安東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 車隊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 車隊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 車隊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 誘餌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 誘餌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 誘餌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 內奸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 內奸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 內奸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 鬼影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 鬼影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 鬼影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 山谷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 山谷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 山谷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 誘敵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 誘敵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 誘敵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壹章 故伎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壹章 故伎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壹章 故伎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二章 有虞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二章 有虞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二章 有虞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三章 反撲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三章 反撲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三章 反撲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四章 拉鋸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四章 拉鋸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四章 拉鋸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五章 穿插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五章 穿插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五章 穿插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六章 價川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六章 價川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六章 價川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七章 圍抄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七章 圍抄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七章 圍抄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八章 堵截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八章 堵截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八章 堵截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九章 堅守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九章 堅守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九章 堅守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十章 阻擊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十章 阻擊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十章 阻擊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壹章 鬥智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壹章 鬥智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壹章 鬥智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二章 血色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二章 血色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二章 血色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三章 平壤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三章 平壤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三章 平壤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四章 風景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四章 風景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四章 風景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五章 休整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五章 休整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五章 休整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六章 漢城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六章 漢城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六章 漢城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七章 弩末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七章 弩末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七章 弩末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八章 間歇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八章 間歇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八章 間歇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九章 霹靂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九章 霹靂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九章 霹靂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十章 砥平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十章 砥平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十章 砥平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壹章 環守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壹章 環守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壹章 環守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二章 亂戰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二章 亂戰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二章 亂戰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三章 殘夜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三章 殘夜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三章 殘夜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四章 機群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四章 機群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四章 機群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五章 蚊子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五章 蚊子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五章 蚊子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六章 血拼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六章 血拼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六章 血拼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七章 強攻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七章 強攻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七章 強攻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八章 圍鬥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八章 圍鬥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八章 圍鬥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九章 阻援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九章 阻援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九章 阻援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十章 雪夜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十章 雪夜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十章 雪夜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壹章 傷春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壹章 傷春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壹章 傷春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二章 偵察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二章 偵察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二章 偵察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三章 良心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三章 良心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三章 良心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四章 華川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四章 華川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四章 華川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五章 襲戰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五章 襲戰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五章 襲戰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六章 手紙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六章 手紙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六章 手紙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七章 猛進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七章 猛進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七章 猛進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八章 磁性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八章 磁性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八章 磁性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九章 後勤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九章 後勤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九章 後勤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十章 護送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十章 護送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十章 護送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壹章 又攻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壹章 又攻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壹章 又攻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二章 空勞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二章 空勞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二章 空勞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三章 回鋒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三章 回鋒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三章 回鋒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四章 險境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四章 險境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四章 險境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五章 掩護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五章 掩護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五章 掩護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六章 渡河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六章 渡河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六章 渡河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七章 代令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七章 代令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七章 代令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八章 靜心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八章 靜心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八章 靜心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九章 悲回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九章 悲回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九章 悲回(三)
- [ 免費 ] 第七十章 狼謀(壹)
- [ 免費 ] 第七十章 狼謀(二)
- [ 免費 ] 第七十章 狼謀(三)
- [ 免費 ] 第七壹章 決斷(壹)
- [ 免費 ] 第七壹章 決斷(二)
- [ 免費 ] 第七壹章 決斷(三)
- [ 免費 ] 第七二章 脅制(壹)
- [ 免費 ] 第七二章 脅制(二)
- [ 免費 ] 第七二章 脅制(三)
- [ 免費 ] 第七三章 夜突(壹)
- [ 免費 ] 第七三章 夜突(二)
- [ 免費 ] 第七三章 夜突(三)
- [ 免費 ] 第七四章 身份(壹)
- [ 免費 ] 第七四章 身份(二)
- [ 免費 ] 第七四章 身份(三)
- [ 免費 ] 第七五章 孤膽(壹)
- [ 免費 ] 第七五章 孤膽(二)
- [ 免費 ] 第七五章 孤膽(三)
- [ 免費 ] 第七六章 狙阻(壹)
- [ 免費 ] 第七六章 狙阻(二)
- [ 免費 ] 第七六章 狙阻(三)
- [ 免費 ] 第七七章 抉死(壹)
- [ 免費 ] 第七七章 抉死(二)
- [ 免費 ] 第七七章 抉死(三)
- [ 免費 ] 第七八章 殘血(壹)
- [ 免費 ] 第七八章 殘血(二)
- [ 免費 ] 第七八章 殘血(三)
- [ 免費 ] 第七九章 瓦全(壹)
- [ 免費 ] 第七九章 瓦全(二)
- [ 免費 ] 第七九章 瓦全(三)
- [ 免費 ] 第壹章 靠港(壹)
- [ 免費 ] 第壹章 靠港(二)
- [ 免費 ] 第壹章 靠港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章 監禁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章 監禁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章 監禁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章 秘審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章 秘審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章 秘審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章 壓驚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章 壓驚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章 壓驚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章 發配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章 發配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章 發配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章 兵殤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章 兵殤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章 兵殤(三)
- [ 免費 ] 第七章 緬甸(壹)
- [ 免費 ] 第七章 緬甸(二)
- [ 免費 ] 第七章 緬甸(三)
- [ 免費 ] 第八章 生存(壹)
- [ 免費 ] 第八章 生存(二)
- [ 免費 ] 第八章 生存(三)
- [ 免費 ] 第九章 迎戰(壹)
- [ 免費 ] 第九章 迎戰(二)
- [ 免費 ] 第九章 迎戰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章 怒江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章 怒江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章 怒江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 門栓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 門栓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 門栓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 雪殤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 雪殤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 雪殤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 借彈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 借彈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 借彈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 死守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 死守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 死守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 回防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 回防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 回防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 天兵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 天兵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 天兵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 壹鼓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 壹鼓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 壹鼓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 風殤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 風殤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 風殤(三)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 馳援(壹)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 馳援(二)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 馳援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 夾擊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 夾擊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 夾擊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壹章 樂極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壹章 樂極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壹章 樂極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二章 孽情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二章 孽情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二章 孽情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三章 邊境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三章 邊境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三章 邊境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四章 雲殤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四章 雲殤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四章 雲殤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五章 質換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五章 質換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五章 質換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六章 情長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六章 情長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六章 情長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七章 背信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七章 背信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七章 背信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八章 回臺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八章 回臺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八章 回臺(三)
- [ 免費 ] 第二九章 戰俘(壹)
- [ 免費 ] 第二九章 戰俘(二)
- [ 免費 ] 第二九章 戰俘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十章 軍殤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十章 軍殤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十章 軍殤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壹章 甄別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壹章 甄別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壹章 甄別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二章 歸管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二章 歸管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二章 歸管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三章 暗謀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三章 暗謀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三章 暗謀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四章 重逢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四章 重逢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四章 重逢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五章 選擇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五章 選擇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五章 選擇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六章 傷殤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六章 傷殤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六章 傷殤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七章 無間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七章 無間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七章 無間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八章 升任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八章 升任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八章 升任(三)
- [ 免費 ] 第三九章 伏蟄(壹)
- [ 免費 ] 第三九章 伏蟄(二)
- [ 免費 ] 第三九章 伏蟄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十章 金門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十章 金門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十章 金門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壹章 炮戰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壹章 炮戰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壹章 炮戰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二章 心殤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二章 心殤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二章 心殤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三章 傷懷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三章 傷懷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三章 傷懷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四章 政戰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四章 政戰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四章 政戰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五章 摸哨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五章 摸哨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五章 摸哨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六章 執著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六章 執著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六章 執著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七章 洪濤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七章 洪濤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七章 洪濤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八章 情殤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八章 情殤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八章 情殤(三)
- [ 免費 ] 第四九章 望鄉(壹)
- [ 免費 ] 第四九章 望鄉(二)
- [ 免費 ] 第四九章 望鄉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十章 歸逃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十章 歸逃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十章 歸逃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壹章 亂炮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壹章 亂炮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壹章 亂炮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二章 傷逝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二章 傷逝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二章 傷逝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三章 作保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三章 作保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三章 作保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四章 民殤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四章 民殤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四章 民殤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五章 饑荒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五章 饑荒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五章 饑荒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六章 人禍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六章 人禍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六章 人禍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七章 苦難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七章 苦難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七章 苦難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八章 忍辱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八章 忍辱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八章 忍辱(三)
- [ 免費 ] 第五九章 榮民(壹)
- [ 免費 ] 第五九章 榮民(二)
- [ 免費 ] 第五九章 榮民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十章 國殤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十章 國殤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十章 國殤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壹章 武鬥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壹章 武鬥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壹章 武鬥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二章 慈悲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二章 慈悲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二章 慈悲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三章 新生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三章 新生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三章 新生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四章 套狼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四章 套狼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四章 套狼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五章 機遇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五章 機遇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五章 機遇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六章 人殤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六章 人殤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六章 人殤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七章 幹校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七章 幹校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七章 幹校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八章 創業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八章 創業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八章 創業(三)
- [ 免費 ] 第六九章 家破(壹)
- [ 免費 ] 第六九章 家破(二)
- [ 免費 ] 第六九章 家破(三)
- [ 免費 ] 第七十章 歷程(壹)
- [ 免費 ] 第七十章 歷程(二)
- [ 免費 ] 第七十章 歷程(三)
- [ 免費 ] 第七壹章 希望(壹)
- [ 免費 ] 第七壹章 希望(二)
- [ 免費 ] 第七壹章 希望(三)
- [ 免費 ] 第七二章 夢殤(壹)
- [ 免費 ] 第七二章 夢殤(二)
- [ 免費 ] 第七二章 夢殤(三)
- [ 免費 ] 第七三章 回暖(壹)
- [ 免費 ] 第七三章 回暖(二)
- [ 免費 ] 第七三章 回暖(三)
- [ 免費 ] 第七四章 黑白(壹)
- [ 免費 ] 第七四章 黑白(二)
- [ 免費 ] 第七四章 黑白(三)
- [ 免費 ] 第七五章 陽春(壹)
- [ 免費 ] 第七五章 陽春(二)
- [ 免費 ] 第七五章 陽春(三)
- [ 免費 ] 第七六章 殘軍(壹)
- [ 免費 ] 第七六章 殘軍(二)
- [ 免費 ] 第七六章 殘軍(三)
- [ 免費 ] 第七七章 舊謀(壹)
- [ 免費 ] 第七七章 舊謀(二)
- [ 免費 ] 第七七章 舊謀(三)
- [ 免費 ] 第七八章 春殤(壹)
- [ 免費 ] 第七八章 春殤(二)
- [ 免費 ] 第七八章 春殤(三)
- [ 免費 ] 第七九章 變天(壹)
- [ 免費 ] 第七九章 變天(二)
- [ 免費 ] 第七九章 變天(三)
- [ 免費 ] 第八十章 平反(壹)
- [ 免費 ] 第八十章 平反(二)
- [ 免費 ] 第八十章 平反(三)
- [ 免費 ] 第八壹章 越戰(壹)
- [ 免費 ] 第八壹章 越戰(二)
- [ 免費 ] 第八壹章 越戰(三)
- [ 免費 ] 第八二章 好報(壹)
- [ 免費 ] 第八二章 好報(二)
- [ 免費 ] 第八二章 好報(三)
- [ 免費 ] 第八三章 還妻(壹)
- [ 免費 ] 第八三章 還妻(二)
- [ 免費 ] 第八三章 還妻(三)
- [ 免費 ] 第八四章 無殤(壹)
- [ 免費 ] 第八四章 無殤(二)
- [ 免費 ] 第八四章 無殤(三)
- [ 免費 ] 第八五章 團聚(壹)
- [ 免費 ] 第八五章 團聚(二)
- [ 免費 ] 第八五章 團聚(三)
杏書首頁 我的書架 A-AA+ 去發書評 收藏 書簽 手機
简
第三九章 夜襲(二)
2018-10-3 18:21
陸軍總司令顧祝同坐鎮徐州以後,與幕僚們商討了現行的國軍作戰體系是否適合當前與共軍的作戰,有人提出了應該參照抗戰後期陸軍組建兵團的辦法,在如此寬闊的地域內進行戰鬥,不可能做到事事由長官部來定奪。而按照現行的國軍高級指揮機構來說,由幾個整編師協同作戰的時候,往往以地域或者任務的名稱作為這個集團軍的名稱,在作戰任務完成以後即撤銷或者改編了。而在組織上,通常是由整編師的師長擔任指揮官,只有極個別的才設立專職指揮官,指揮機構也非常簡單的,也就有壹個參謀處、幾個參謀、電務員、副官再加上壹個班或者壹個連的衛士而已。沒有專業參謀群的高級司令部,這樣的指揮機構也只能承擔上傳下達的工作,根本很難有效地擔任大軍的指揮任務,再加上臨時任命指揮官的時候,許多師長之間本來是平級的關系,這個時候卻要被領導,自然會很不愉快,所以也常常發生互不協作的場面。
徐州與鄭州綏靖公署被撤銷之後,對於如何指揮這兩個單位之下眾多的軍隊,有效地進行作戰,也成了壹個必須要解決的問題,於是,在又壹次對共產黨山東解放區的重點進攻之前,兵團也就應運而生了。的確,在這個時候,成立專門的兵團司令部顯得尤其重要。
這次對山東解放區的攻勢發動之前,顧總司令專門成立了三個兵團,這些兵團都設有專門的司令和獨立的司令部,向上直接由陸軍總司令部徐州司令部指揮,向下也有技術能力協調指揮數個整編師進退攻防。
第壹兵團以張林福的整編七十四師作為主力,包括整編二十五、二十八、五十七、六十五、七十四和八十三六個師,共十九個旅,司令官為湯恩伯。
第二兵團以整編第二十七軍為基礎組建,主力部隊為邱雨青的第五軍,包括第五軍,整編七十二,七十五和八十五三個師,共十個旅,司令官是王敬久。
第三兵團以整編第十九軍作為基礎,主力部隊便是胡從俊有整編第十壹師,包括第七軍、整編第九、十壹、二十、四十八、六十四、八十四六個師,合計為十八個旅,司令官為歐震。
這次對山東解放區的進攻,第壹兵團從臨沂附近出發,向北沿著臨蒙公路向北推進,為此湯恩伯把自己的指揮部便設在了臨沂,只是在他的這個兵團裏,雖說他是主指揮官,但是面對整編七十四師這樣被蔣主席作為模範的王牌,指揮起來卻有些力不從心。大戰壹開始的時候,張林福便對上面把自己的整編七十四師開進山區很不滿意,整編七十四師的裝備並不適合山地作戰,這個師也沒有參加過當年的滇緬會戰,在山區作戰的經驗並不充足,所以張林福當著湯司令的面就丟下了壹句話:“把我們七十四師往山區裏送,那就是等於要我們去死!那好,我就去死給妳們看!”面對張林福如此不滿意的狂言,作為司令官的湯恩伯竟然無言以對,只能好言安慰壹番。事情雖說就這麽過去,但是,這也許就是壹個十分不祥的預示!
第二兵團位於津浦鐵路的泰安沿線,第五軍與整編十壹師的任務相當,只不過他們是從鐵路線附近向東攻擊前進,目標是剛剛被共軍奪占不久的萊蕪城。第五軍與整編十壹師的距離倒是最近的。
整編十壹師歸屬於第三兵團節制,除了整編十壹師之外,第三兵團的大部還在棗莊、滕縣等津浦鐵路線和運河附近,這個時候也向東北方向進發,以期在蒙陰附近會合。
又壹場的大戰就這樣在齊魯大地上拉開了序幕!
※※※
十壹旅當先著已然來到了蒙山的腳下。
沂蒙山區,其實不過是壹個人文的地理名稱,而並非是真正意義上的山脈或者丘陵。沂,指得就那條發源於蒙山的沂河,源出於南麻附近,向南經過臨沂後流入江蘇境內;蒙,指得是位於山東省南部的蒙山,這是山東泰沂山脈的壹個分支,呈西北—東南走向,最高峰是位於平邑縣的龜蒙頂,海拔有壹千壹百五十六米,也是山東省僅次於泰山的第二高峰。這片區域位於津浦鐵路以東,膠濟鐵路以南、棗莊、臨沂、日照壹線以北,東到大海之間,面積有上萬平方公裏,包括了數十個縣。沂蒙山區有壹種特有的地貌景觀,那就是許多的山峰頂部都十分平展開闊,峰巔周圍峭壁如削,峭壁下面坡度由陡到緩,遠遠看去,就好象是戴著壹個平頂的帽子。這種山頭在地理學上被稱之為方山,而當地人卻有壹個特殊的名字,叫做“崮”,據說沂蒙山區裏的“崮”,有名的就有上百座之多。
前面就是進入沂蒙山區的壹個隘口——白馬關。名字雖叫做關,但是實質上只是兩座高山中間所夾的壹座小山,北面的山峰名叫做魚鱗山,南面的山峰叫做大望山,從平邑通往蒙陰的大路就從這兩山之間所夾的小山上經過,所以這個小山成了壹條咽喉之道,古時候曾在這裏修築過關口,只是年代久遠,關城早已經廢棄了,此時,倒是有壹個村子位於這裏,於是這個小山也成了共軍的防衛重點。
果然,搜索隊回來報告,白馬關有共軍的主力部隊把守,無法通過,此時,搜索隊已經與白馬關陣地上的共軍接上了火,打得正在激烈之中。
張賢來到了邊上的壹座稍高壹些的山頭,舉起望遠鏡,向著槍響的地方看去,在新綠的樹叢之中,隱約可以看到有共軍在來回得活動著,那裏已經修築了陣地,望遠鏡裏還可以看到用石頭壘起的防禦工事。
“怎麽樣?”楊濤旅長也走了過來,問著張賢。
張賢把手中的望遠鏡遞給了他,楊濤舉起望遠鏡向著對面的山上看去。
“這真是壹個易守難攻的地方!”張賢有些感慨地道:“看來,我們如果不展開重兵,是奪不下這個關口的!”
楊濤壹邊看著,壹邊點了點頭,然後把望遠鏡又遞還給了張賢。對著張賢道:“我看南面的幾個小山頭可以先奪下來,只在奪下來後,那麽便有了突破口!”
張賢再壹次舉起望遠鏡,正如楊旅長所說得壹樣,南邊有三個小山頭緊挨著路邊,就像是鉗子壹樣扼住了交通的咽喉,而主陣地正在這三個小山頭之北,同樣是位於路邊,因為地勢險要,易守難攻,所以便於大規模地布兵,很顯然,共軍是把主要陣地放在了北面的山崗之上,而在南邊的幾個小山頭上,只布置了不多的兵力。畢竟那小山頭過於平緩,而且面積也小,相對來說,不利於防守。
看完了地形,張賢也點著頭,對著楊濤道:“不錯,南邊的山頭要是能夠拿下來,我們就可以用壹支部隊迂回到他們主陣地的側背,從那個方向夾擊,這個關口也就不攻自破了!”
“好!我們就這麽打!”楊濤很是贊賞地道。
可是,要想奪下南邊的那幾個山頭,又談何容易呢?此時,對手是居高臨下,而自己卻是向上仰攻,便是炮火再猛,只怕要想奪取陣地,也要付出對方雙倍的代價。
楊濤看了看自己的手表,此時已然是下午三點多鐘了,初春的白天雖然在漸漸變長,但是在這個時刻要想發動進攻,顯然來不及了,只怕戰鬥才剛剛打響,天就要黑了。
“看來,我們只好要等到明天再說了!”楊濤有些無奈地道。
張賢也看了看自己的手表,時間上的確並不允許他們發動進攻,當下點著頭,卻又有些擔憂地道:“是呀,我們為今之計是要找壹個宿營地,等明日壹早再發動進攻!只是,這個白馬關以西的地方都是壹片開闊的平地,連個守的地方都沒有,晚上萬壹敵軍過來偷襲,那可就有些麻煩!”
“嗯!”楊濤點著頭,表示同意:“妳說的這個問題還真要當心,我們壹起去附近轉壹轉,看看哪裏適合宿營!”
“是!”張賢答應著。
※※※
楊濤命令著全旅停止了前進,帶著張賢和幾個作戰參謀,登上了邊上更高的壹處山崗,向西面的遠處望去,只見眼底壹片青青的麥苗,如同壹層碧綠的地毯鋪在蒼天之下,遠處的村落掩印在初綠的樹林之間,炊煙裊裊,如果不是耳邊還傳來隱約的對射的槍聲,這便是壹付美麗的初春鄉野圖。
這個時候,張賢和眾人也沒有心情觀賞初春傍晚的美景,他們還在找尋著能夠讓幾千人安全過夜的宿營地。
“那邊有壹道高壟,也不知道是什麽地方!”壹個參謀指著遠處三四裏之外壹條高出四周的土堆,這樣地說著。
張賢與楊濤都順聲望去,果然,在蒼翠的原野間,壹片平整的地面上壟起了壹道很高的土堆,足有兩三裏地長,南北向地橫在了這片開闊的平地之上。
“走,到那邊去看看!”楊濤向大家說著。
當下,幾個人下了山崗,騎著馬來到了這個土堆之側,才發現這片土堆足有近十米高,便是上面也有十多米寬。這附近又沒有河流,這道土壟肯定不會是大堤,很顯然是古代土夯的城墻,這裏很可能曾經是古時候的壹座城市遺址,只是由於年代過於久遠,這座古城已經湮滅在了歷史的長河裏,只剩下了這壹段高出地表城墻還矗立在這片荒原之上,但是經過了不知多少年的櫛風沐雨,這段城墻也塌陷了下來,與四周的土城融合成了壹體,上面已經長滿了荒草。
“呵呵,這真是天住我也!”楊濤旅長大笑了起來,高聲對著張賢道:“張賢呀,這道土堆就是壹個天然的屏障呀!”
“是!”張賢隨聲附和著:“我們可以把部隊在這個土堆之後就宿,同時派兩個營或者壹個加強營駐守在這個土堆之上,構築好工事,做好嚴密的警戒;再在後面配以炮兵支援,直接把炮口對準這個土堆之前;這樣,便是共軍晚上過來偷襲,我們也可以從容面對!”
“是呀!”楊濤也道:“我們和共軍打了這麽久,這些共軍就是數夜貓子的,總是在晚上對我們發動襲擊。想當年打鬼子的時候,我們也沒有這麽累過!讓人想睡個好覺都不行!”
“呵呵,是呀!”張賢回答著,忽然想起當年和馬文龍曾在壹起合兵,對鬼子發動過壹次夜襲,那壹次是襲擊壹個日軍的正在修建的機場,成功地解救了上千名的國軍與共軍的戰俘,只是也令很多的戰俘死在了亂槍之下。想到這裏,他忽然壹動,對著楊濤道:“旅長,為什麽我們總要等著共軍來對我們發動夜襲,而我們為什麽不主動地去向他們發動夜襲呢?如果我們也給他們來壹個夜襲,定然可以打他們壹個措手不及!”
聽到這話,楊濤不由得驀然壹楞!
徐州與鄭州綏靖公署被撤銷之後,對於如何指揮這兩個單位之下眾多的軍隊,有效地進行作戰,也成了壹個必須要解決的問題,於是,在又壹次對共產黨山東解放區的重點進攻之前,兵團也就應運而生了。的確,在這個時候,成立專門的兵團司令部顯得尤其重要。
這次對山東解放區的攻勢發動之前,顧總司令專門成立了三個兵團,這些兵團都設有專門的司令和獨立的司令部,向上直接由陸軍總司令部徐州司令部指揮,向下也有技術能力協調指揮數個整編師進退攻防。
第壹兵團以張林福的整編七十四師作為主力,包括整編二十五、二十八、五十七、六十五、七十四和八十三六個師,共十九個旅,司令官為湯恩伯。
第二兵團以整編第二十七軍為基礎組建,主力部隊為邱雨青的第五軍,包括第五軍,整編七十二,七十五和八十五三個師,共十個旅,司令官是王敬久。
第三兵團以整編第十九軍作為基礎,主力部隊便是胡從俊有整編第十壹師,包括第七軍、整編第九、十壹、二十、四十八、六十四、八十四六個師,合計為十八個旅,司令官為歐震。
這次對山東解放區的進攻,第壹兵團從臨沂附近出發,向北沿著臨蒙公路向北推進,為此湯恩伯把自己的指揮部便設在了臨沂,只是在他的這個兵團裏,雖說他是主指揮官,但是面對整編七十四師這樣被蔣主席作為模範的王牌,指揮起來卻有些力不從心。大戰壹開始的時候,張林福便對上面把自己的整編七十四師開進山區很不滿意,整編七十四師的裝備並不適合山地作戰,這個師也沒有參加過當年的滇緬會戰,在山區作戰的經驗並不充足,所以張林福當著湯司令的面就丟下了壹句話:“把我們七十四師往山區裏送,那就是等於要我們去死!那好,我就去死給妳們看!”面對張林福如此不滿意的狂言,作為司令官的湯恩伯竟然無言以對,只能好言安慰壹番。事情雖說就這麽過去,但是,這也許就是壹個十分不祥的預示!
第二兵團位於津浦鐵路的泰安沿線,第五軍與整編十壹師的任務相當,只不過他們是從鐵路線附近向東攻擊前進,目標是剛剛被共軍奪占不久的萊蕪城。第五軍與整編十壹師的距離倒是最近的。
整編十壹師歸屬於第三兵團節制,除了整編十壹師之外,第三兵團的大部還在棗莊、滕縣等津浦鐵路線和運河附近,這個時候也向東北方向進發,以期在蒙陰附近會合。
又壹場的大戰就這樣在齊魯大地上拉開了序幕!
※※※
十壹旅當先著已然來到了蒙山的腳下。
沂蒙山區,其實不過是壹個人文的地理名稱,而並非是真正意義上的山脈或者丘陵。沂,指得就那條發源於蒙山的沂河,源出於南麻附近,向南經過臨沂後流入江蘇境內;蒙,指得是位於山東省南部的蒙山,這是山東泰沂山脈的壹個分支,呈西北—東南走向,最高峰是位於平邑縣的龜蒙頂,海拔有壹千壹百五十六米,也是山東省僅次於泰山的第二高峰。這片區域位於津浦鐵路以東,膠濟鐵路以南、棗莊、臨沂、日照壹線以北,東到大海之間,面積有上萬平方公裏,包括了數十個縣。沂蒙山區有壹種特有的地貌景觀,那就是許多的山峰頂部都十分平展開闊,峰巔周圍峭壁如削,峭壁下面坡度由陡到緩,遠遠看去,就好象是戴著壹個平頂的帽子。這種山頭在地理學上被稱之為方山,而當地人卻有壹個特殊的名字,叫做“崮”,據說沂蒙山區裏的“崮”,有名的就有上百座之多。
前面就是進入沂蒙山區的壹個隘口——白馬關。名字雖叫做關,但是實質上只是兩座高山中間所夾的壹座小山,北面的山峰名叫做魚鱗山,南面的山峰叫做大望山,從平邑通往蒙陰的大路就從這兩山之間所夾的小山上經過,所以這個小山成了壹條咽喉之道,古時候曾在這裏修築過關口,只是年代久遠,關城早已經廢棄了,此時,倒是有壹個村子位於這裏,於是這個小山也成了共軍的防衛重點。
果然,搜索隊回來報告,白馬關有共軍的主力部隊把守,無法通過,此時,搜索隊已經與白馬關陣地上的共軍接上了火,打得正在激烈之中。
張賢來到了邊上的壹座稍高壹些的山頭,舉起望遠鏡,向著槍響的地方看去,在新綠的樹叢之中,隱約可以看到有共軍在來回得活動著,那裏已經修築了陣地,望遠鏡裏還可以看到用石頭壘起的防禦工事。
“怎麽樣?”楊濤旅長也走了過來,問著張賢。
張賢把手中的望遠鏡遞給了他,楊濤舉起望遠鏡向著對面的山上看去。
“這真是壹個易守難攻的地方!”張賢有些感慨地道:“看來,我們如果不展開重兵,是奪不下這個關口的!”
楊濤壹邊看著,壹邊點了點頭,然後把望遠鏡又遞還給了張賢。對著張賢道:“我看南面的幾個小山頭可以先奪下來,只在奪下來後,那麽便有了突破口!”
張賢再壹次舉起望遠鏡,正如楊旅長所說得壹樣,南邊有三個小山頭緊挨著路邊,就像是鉗子壹樣扼住了交通的咽喉,而主陣地正在這三個小山頭之北,同樣是位於路邊,因為地勢險要,易守難攻,所以便於大規模地布兵,很顯然,共軍是把主要陣地放在了北面的山崗之上,而在南邊的幾個小山頭上,只布置了不多的兵力。畢竟那小山頭過於平緩,而且面積也小,相對來說,不利於防守。
看完了地形,張賢也點著頭,對著楊濤道:“不錯,南邊的山頭要是能夠拿下來,我們就可以用壹支部隊迂回到他們主陣地的側背,從那個方向夾擊,這個關口也就不攻自破了!”
“好!我們就這麽打!”楊濤很是贊賞地道。
可是,要想奪下南邊的那幾個山頭,又談何容易呢?此時,對手是居高臨下,而自己卻是向上仰攻,便是炮火再猛,只怕要想奪取陣地,也要付出對方雙倍的代價。
楊濤看了看自己的手表,此時已然是下午三點多鐘了,初春的白天雖然在漸漸變長,但是在這個時刻要想發動進攻,顯然來不及了,只怕戰鬥才剛剛打響,天就要黑了。
“看來,我們只好要等到明天再說了!”楊濤有些無奈地道。
張賢也看了看自己的手表,時間上的確並不允許他們發動進攻,當下點著頭,卻又有些擔憂地道:“是呀,我們為今之計是要找壹個宿營地,等明日壹早再發動進攻!只是,這個白馬關以西的地方都是壹片開闊的平地,連個守的地方都沒有,晚上萬壹敵軍過來偷襲,那可就有些麻煩!”
“嗯!”楊濤點著頭,表示同意:“妳說的這個問題還真要當心,我們壹起去附近轉壹轉,看看哪裏適合宿營!”
“是!”張賢答應著。
※※※
楊濤命令著全旅停止了前進,帶著張賢和幾個作戰參謀,登上了邊上更高的壹處山崗,向西面的遠處望去,只見眼底壹片青青的麥苗,如同壹層碧綠的地毯鋪在蒼天之下,遠處的村落掩印在初綠的樹林之間,炊煙裊裊,如果不是耳邊還傳來隱約的對射的槍聲,這便是壹付美麗的初春鄉野圖。
這個時候,張賢和眾人也沒有心情觀賞初春傍晚的美景,他們還在找尋著能夠讓幾千人安全過夜的宿營地。
“那邊有壹道高壟,也不知道是什麽地方!”壹個參謀指著遠處三四裏之外壹條高出四周的土堆,這樣地說著。
張賢與楊濤都順聲望去,果然,在蒼翠的原野間,壹片平整的地面上壟起了壹道很高的土堆,足有兩三裏地長,南北向地橫在了這片開闊的平地之上。
“走,到那邊去看看!”楊濤向大家說著。
當下,幾個人下了山崗,騎著馬來到了這個土堆之側,才發現這片土堆足有近十米高,便是上面也有十多米寬。這附近又沒有河流,這道土壟肯定不會是大堤,很顯然是古代土夯的城墻,這裏很可能曾經是古時候的壹座城市遺址,只是由於年代過於久遠,這座古城已經湮滅在了歷史的長河裏,只剩下了這壹段高出地表城墻還矗立在這片荒原之上,但是經過了不知多少年的櫛風沐雨,這段城墻也塌陷了下來,與四周的土城融合成了壹體,上面已經長滿了荒草。
“呵呵,這真是天住我也!”楊濤旅長大笑了起來,高聲對著張賢道:“張賢呀,這道土堆就是壹個天然的屏障呀!”
“是!”張賢隨聲附和著:“我們可以把部隊在這個土堆之後就宿,同時派兩個營或者壹個加強營駐守在這個土堆之上,構築好工事,做好嚴密的警戒;再在後面配以炮兵支援,直接把炮口對準這個土堆之前;這樣,便是共軍晚上過來偷襲,我們也可以從容面對!”
“是呀!”楊濤也道:“我們和共軍打了這麽久,這些共軍就是數夜貓子的,總是在晚上對我們發動襲擊。想當年打鬼子的時候,我們也沒有這麽累過!讓人想睡個好覺都不行!”
“呵呵,是呀!”張賢回答著,忽然想起當年和馬文龍曾在壹起合兵,對鬼子發動過壹次夜襲,那壹次是襲擊壹個日軍的正在修建的機場,成功地解救了上千名的國軍與共軍的戰俘,只是也令很多的戰俘死在了亂槍之下。想到這裏,他忽然壹動,對著楊濤道:“旅長,為什麽我們總要等著共軍來對我們發動夜襲,而我們為什麽不主動地去向他們發動夜襲呢?如果我們也給他們來壹個夜襲,定然可以打他們壹個措手不及!”
聽到這話,楊濤不由得驀然壹楞!